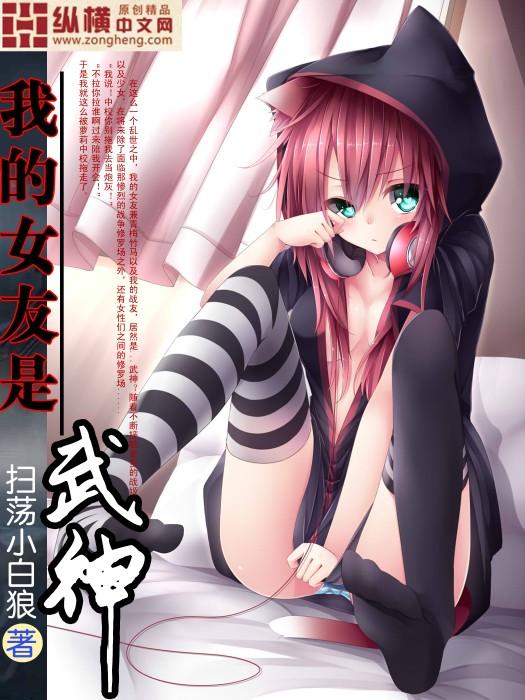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情剑在线阅读 > 第一章 小店怪客(第1页)
第一章 小店怪客(第1页)
秋,木叶萧萧。
街上的尽头,有座巨大的宅院,看来也正和枝头的黄叶一样,已到了将近枯落的时候。
漠北之地,除了飞沙,剩下最多的便是雪山,这里方圆百里都是一样的光景,然而这里山高皇帝远,难以约束,是以这里成为了江湖中有罪的,没罪的这类人的藏身之地,此地更有雪山派、天山派、凌霄城、血刀门四大门派争夺之地。这里可以说是人间天堂,已是人间地狱。
在潼关走入三百里,便属关西,有个鸡毛小店,也可以说是客栈,没有牌匾,也没有名字,但这小间客栈接待的江湖过客不计其数,卖些粗粝的饮食,后面有十三五间简陋的客房,店主孙驼子是个残废的侏儒。据说他当年也是名震江湖的侠客,不知为何会到这西北之地来经营这小小的客栈,或许是看破了。
他虽然明知道这客栈里绝不会有什么高贵的主顾,但却宁愿在这里等着些卑贱的过客,进来以低微的代价换取食宿。
他宁愿在这里过他清苦卑贱的生活,也不愿走出去听人们的嘲笑,因为他已懂得无论多少财富,都无法换来心头的平静,远离江湖,心的归处。
他当然是寂寞的。
而,就在今天,正午的时候,这小店里来了位与众不同的客人,其实他穿的也并不是什么很华贵的衣服,长得也并不特别。
他身材虽很高,面目虽也还算得英俊,但看来却有些憔翠,眼神却依然充满英气,同他来的,还有一位女子,她的妆容亦是十分朴素,一张长又薄的轻纱遮住面孔,隐约间能看得出,这个女子面容惊人,不是因为她难看,而是因为她太好看。
他实在是个很平凡的人。
但孙驼子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男人的背上还负着一件重物,用麻布包裹起来的的一件重物。
这个男人对孙驼子的残废并没有嘲笑,也没有注意,更没有装出特别怜悯的同情神色。
这种同情有时比嘲笑还要令人受不了。
男人和女人坐到了最角落的一张桌子上,他点了一壶酒,他对于酒既不挑剔,也不赞美。他根本就很少说话,那个女人也少说话。
又要一碟豆干、一碟牛肉、两个馒头还有一碗面。
那碗面是为这个女人叫的,男人不吃东西,只吃酒。
一壶酒喝完了,他就叫孙驼子再加酒,不消片刻,七壶酒已喝光了。
孙驼子也是个酒徒,对这人的酒量他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能喝完七壶酒而不醉的人,他一生中还未见到过。
有时他也忍不住问问这人的姓名,却还是忍住了,因为知道即使问了,也不会得到答覆。
孙驼子并不是个多嘴的人。
不多时,就看到有两个人骑着马从前面绕过来。
客栈外里骑马的人很多,但骑这种马的人不多,因为这是凌霄城的马,孙驼子也不禁多瞧了两眼。
只见这两人都穿着杏黄色的长衫,前面一人浓眉大眼,后面一人鹰鼻如,两人凳下都留着短须,看起来都只有三十多岁。
这两人相貌并不出众,但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却极耀眼,两人都没有留意孙驼子,却不时仰起头向高墙内探望。
孙驼子继续磨他的豆腐。
他知道这两人绝不会是他的主顾。
只见两人走过客栈,果然又绕到前面去了,可是还没过多久,两人又从另一头绕了回来。
这次两人竟在小店前下了马。
孙驼子脾气虽古怪,毕竟是做生意的人,立刻停下手问道:“两位可要吃喝点什么?”
浓眉大眼的黄衫人道:“咱们什么也不要,只想问你两句话。”
孙驼子又开始磨豆腐,他对说话并不感兴趣。
鹰鼻如勾的黄衫人忽然笑了笑,道:“咱们就要买你的话,一句话一钱银子,如何?”
孙驼子的兴趣来了,点头道:“好。”
他嘴里说着话,已伸出了一根手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