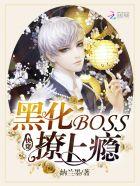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佣兵日记前锋最后去哪了 > 第222章(第1页)
第222章(第1页)
&ldo;杂种!&rdo;他突然骂道,他额头上的青筋暴起,&ldo;我不想杀你!所以你也别撩动我的底线,有枪的人是我!你这只来自亚洲的杂种狗!&rdo;
&ldo;对啊!我才感觉到!其实我手里也拿着枪!&rdo;我的精神突然爆发,我力大无穷的左手快速向前抓住了伯莱塔手枪的套筒,然后迅速发力,把套筒完全握住,这家伙想扣动扳机,但子弹无论如何也别想从枪管中喷出,于此同时,我慢慢侧身,一只手抓住了波拉丹诺维奇尸体上的那支ppk手枪,然后ppk的黑洞洞的枪口就顶住了胖子的太阳穴。
&ldo;啊哈!现在我们都有枪了!&rdo;我依旧握住他手枪的套筒,这家伙憋得胖脸通红,下巴上的赘肉上跳下跳,他不断地在我的枪口下摇头,他不敢直视我了,许久,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好像在说:&lso;好吧&rso;
&ldo;你他妈在说什么!&rdo;我恶狠狠地咆哮道,一边压下了ppk手枪的机头,&ldo;如果你想活命??&rdo;
&ldo;合作是吗!你这个狗杂种!&rdo;宁死不屈,精神可嘉,但这招在我的枪口下可没用。
&ldo;对对对!你还算识相!肥佬!&rdo;
&ldo;好吧!小偷!咱们干脆都放下手中能要人性命的家伙事,进车里谈一谈吧。&rdo;他指了指枯焦的林子,然后他把手伸进西裤口袋,按动了汽车报警器的开关,这很可能是在和他的同伙发信号,那边的车子有了响应,叫了两声,我吞了口唾沫,下了他的伯莱塔手枪,并顺手抄下了他藏在脚踝上的袖珍转轮手枪,现在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无毒无害的德国肥佬,不,他也未必是德国人,他太不谨慎了。
&ldo;如果要我知道车里有半打步枪指着我!你同样也会死的很惨!&rdo;我真正的做到了反客为主,我挟持着这个嘴里叽里呱啦叫骂的死胖子走向了他那辆在林子中等待主人的奔驰越野车,驾驶员可能已经死在里面了,我看得到一棵小树砸进了车子的前挡风玻璃。
我们进入车内,我小心的用手枪短小的枪管拨开驾驶座的车门,看到西装革履的司机直接被树干刺进了面门,死相惨不忍睹。在确认一切无误后,我和胖子都坐进了车子的后排座,我们可能要进行一次谈判了。
这家伙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给自己点上一支烟,叼在嘴上,然后不就水生生咽下了几粒可能有镇静作用的药丸,那些药丸的个头个个都不比一枚50的机枪弹小多少,他喘着粗气,我不安的看着他,我把ppk手枪放在大腿上,我很明白,他伤不了我。
我脱掉夹克,汗水湿透了全身,虽然现在是寒冷的冬天。
我们坐在车里很长时间谁都没有蹦出一个字来,我们都惊魂未定,为刚才没有互相送给对方一枪而暗自庆幸,这只能是暗自,因为我们此时都心存警惕,而我,更是心存侥幸,这家伙铁定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如果还不能找到任何线索,我还不如死在柏林为好。
许久,我用并不熟练的德语吐出几个字来:&ldo;你为什么要杀了波拉丹诺维奇?&rdo;
&ldo;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rdo;他镇静了下来,慢慢说道,&ldo;可能是自由吧!&rdo;
自由!
不,不,我是孙振,我是死神。
&ldo;自由!&rdo;我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波澜,我的声音变得有些歇斯底里,野兽似地咆哮带出了我那颗与自由久违的心,&ldo;自由……我的天,自由,可是你为布莱克那个狗杂种工作!&rdo;
&ldo;闭嘴!你这个该死的、污秽的小偷!你这头蠢驴!二十年前,苏黎世班霍夫大道上的五根炸药送走了我儿子!&rdo;
&ldo;什么?&rdo;
&ldo;天哪!二十年前!我儿子以西德大使书记的身份在苏黎世被布莱克的手下炸得尸骨无存!你却说我在为他工作!是啊,必要的话我可以承认自己是个&lso;双面间谍&rso;,我叫圣德西,圣德西?弗里德里希。&rdo;
这家伙在他妈的说些什么该死的劳什子!我不懂!我不懂!
不,镇静,镇静。
我是孙振,我是他妈的死神。
但我他妈的就是镇静不了!这是怎么搞的!
&ldo;我的天!我为什么要相信你!难道我不能把你看做布莱克送给我的鱼饵!&rdo;
&ldo;你也可以能!但我劝你还是相信的为好,到头来你还是一个死!你这个该死的??&rdo;
&ldo;闭嘴!&rdo;我需要安静,有必要的话可以吞两粒比50机枪弹尺寸还大的黑色药丸,&ldo;好吧,我暂且相信你,我叫什么想必你已经知道,那么,下面我问你,刚才你们在干什么!既然我们要合作!那就全都告诉我!&rdo;
&ldo;不!合作需要筹码!我的筹码已经摆明了,我以我在天上的儿子起誓,我会给你关于军刀部队所有的情报,我为这个该死的布莱克&lso;工作&rso;了十五年,从我儿子遇害那年起,我就一直以一个俄国人的身份像一只蛔虫一样寄生在这庞大组织的内部,他们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但前提是,我要自由!&rdo;
&ldo;你的意思是要钱吗?&rdo;我有些吃惊,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ldo;自由……这很容易,我可以给你二百万美元或者更多,你可以利用这些钱逃的天涯海角,百慕大或者索马里都可以!&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