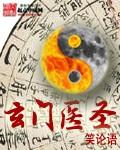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天骄作者白芥子 > 第93页(第1页)
第93页(第1页)
巳时末,风雪已停,承国公府大门洞开,来客熙熙。
怀王府的车子至正门口停下,萧莨迎上前,将祝鹤鸣引进府中。
祝鹤鸣一路走笑问萧莨:“我与雁停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他近来可好?”
萧莨淡声回答:“还是老样子,依旧出不得门,雁停说想见兄长,还得麻烦兄长过去一趟。”
“那倒是不麻烦,我也正说想去看看他,”祝鹤鸣说着一顿,停住脚步,侧目望向身旁的萧莨,问他,“二郎可是有烦心事?”
“不曾,兄长多心了。”萧莨垂眸淡道。
祝鹤鸣打量着他,目光中带着些揣度之意,顿了一顿,到底没再多问,去了祝雁停那边。
祝鹤鸣进门时,祝雁停正心不在焉地独自下棋,祝鹤鸣一见他模样眉头便拧了起来,坐下问他:“你怎瘦了这么多?这几个月没好好养着吗?”
祝雁停随口解释:“我无事,只是胃口不太好而已,其他已无大碍了,兄长无需挂虑。”
“当真?”
“嗯,”祝雁停轻颔首,“真的无事。”
“你夫君又是怎么回事?今日我见他态度似越发冷淡了,提起你时也一样,可是被他知晓了什么?”
祝雁停本不想说,但被祝鹤鸣这么盯着,只得说了实话:“他确实知道了我的目的,还知道关于刘崇阳的一些事情……”
祝鹤鸣眼瞳轻缩:“他知道了,但不肯帮我们是吗?”
沉默一阵,祝雁停低喃:“是我没用。”
祝鹤鸣一声长叹:“其实我早该猜到的,……罢了,也不怪你。”
祝雁停摇头,坚持道:“是我没用,答应了兄长的事情却没办好。”
“你与他起了争执?”
祝雁停抿起唇角,抬眸望向祝鹤鸣,犹豫问他:“兄长,你可知刘崇阳他私底下究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会叫贺家的人盯上他?”
祝鹤鸣面不改色:“你可是知道了什么?”
“……我不知道,萧莨他什么都不肯跟我说,还打发了我身边的下人,但是兄长,刘崇阳此人,你当真觉得可用吗?”
祝鹤鸣轻啜一口茶,冷了神色:“他确实有用,但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一个人,小心思多得很,眼下我们只能靠他,……待有一日,我迟早要与他清算。”
“兄长,”祝雁停提醒他,“那虞道人虽是刘崇阳带去你跟前的,与刘崇阳未必就是一条心,他才是皇帝面前真正能说得上话的人,你须得牢牢抓着他才是。”
祝鹤鸣点头:“我知,你不必操心这些,我心里都有数。”
祝雁停的眉宇间依旧有忧色,心下总是不得安稳。
祝鹤鸣劝他道:“你别想太多,忧思过重容易坏了身子。”
祝雁停心里不得劲,心不在焉地应下:“……嗯。”
晌午时分,正院的大堂里高朋满座、宾客云集,珩儿还醒着,被人抱着出来转了一圈,大眼珠子吱溜转,逢人就笑,得了无数夸赞,到处是欢声笑语。
门房上,守门的家丁喜气洋洋地凑在一块,正吃着上头赏下的酒肉,直到门外传来一阵不合时宜的马急蹄声,又接着一声凄厉的烈马嘶鸣。
一个家丁出来瞧,就见一匹高大黑马累瘫在府门前,一身铠甲的士兵从雪地里爬起,跌跌撞撞地冲上石阶,攥住那家丁,赤红着双目嘶哑声音道:“快!快带我进去!我奉国公之命前来报信,快带我进去!”
萧莨匆匆出来,在二门上碰到被人引进来的送信兵,对方见着他,膝盖一软,单腿重重跪到地上,满是血丝的双眼里流下眼泪,哽咽道:“十日前世子领兵收复凉州骆城失地,与敌军在骆城山前峡谷地带相遇,混战中世子被敌军冷箭洞穿腰腹,当场身死……”
萧莨愕然,待到回神时已不自觉地踉跄往后跌了一步,瞬间红了眼眶,紧握住拳头下意识地问对方:“你说什么?”
跪在地上的人痛哭失声:“世子,世子他战死沙场了啊!”
花厅里,女眷设宴在此,正衣香鬓影、红飞翠舞,好不热闹。
卫氏手中抱着珩儿,杨氏坐于她身侧,旁边围了一圈人,都在争抢着逗弄这怎么逗都不哭的小娃娃,不时有笑语传出。
直到有下人满头大汗急匆匆地进门来,也顾不得还有众多外人在,抖索着身子跪到地上,艰声禀报:“夫人、少夫人,方、方才,国公爷派来的送信兵说、说世子在战场之上被人偷袭,中了冷箭,当场就身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