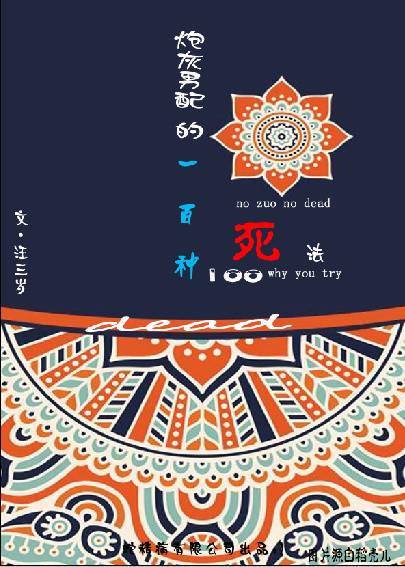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老九门陈皮阿四番外篇 > 第39章(第1页)
第39章(第1页)
秦艽洗好澡,躺回床上,从未觉得如此静谧,是啊,这样一个院子里,只有她和陈皮两个人了,要说什么话,别人也听不见,要做什么事,别人也不知道。
秦艽翻来覆去,没了旁边的人,竟然有些睡不着,这样想着,秦艽有些恼了自己:哎呀,我可没想做什么呢。想做什么的,明明只有那个小流氓!快睡着,快睡着吧。
可是陈皮洗得太快。
陈皮回房的时候,秦艽头脑还清醒得不得了,真是气人。秦艽只好闭了眼,装作熟睡。
陈皮进了房就看见艽艽乖巧地躺在床里边,刚洗过澡,脸上还润润的,透着水汽。热水浸泡过的身子,可以想像是又软又暖。
发尾还有些湿,蜿蜒着伸进了里衣,引着陈皮的视线往里瞧,发梢渗着水,渐渐濡湿了薄薄的一层里衣,透出了紧贴着的肚兜的花色。
艽艽在衣物上面不介意,花枝招展的颜色太贵了,于是买的都是素色的布料,又不会绣工,肚兜都是纯色,青青的棉布,很是寡淡。
可是一旦有了肚兜下面小小的波澜起伏,那寡淡便生出了些旖旎的风味来。
陈皮咽了咽口水,终于还是走上前来,无师自通一般,手从衣服下摆探了进去,却不像平时,只停留在腹部,随着腰线往上,一寸寸地探索着,只觉手下一片柔嫩,真是软的不像话。
秦艽有些怕,紧闭了眼,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却又有着浅浅的期待。秦艽被自己心底的期待吓了一跳,羞得连脖子都红了一片,睫毛急剧地颤动着。
终于,手终于到达了最柔软的地方,可惜手的主人还没意识到,粗粗一扫,便碰到了柔软上的红嫩,秦艽只觉又痒又苏,不禁婉转出了一声低哼。
陈皮却不敢再动,手虚虚罩在红嫩之上,随着秦艽的轻颤,不时碰到那娇嫩,满手滑腻。
陈皮手一软,差点撑不住自己,就要倒在秦艽身上。陈皮咬牙撑住,还是没忍住放手下去,揉了揉那片软肉。
秦艽脑海中好似过着元宵,砰砰砰放了无数的礼花,那礼花绽得热闹非凡,比月亮还要亮堂。
天空下是绵延了一整条街的灯会,望不见头,只看到一盏盏灯笼亮了起来,那星星点点的灯火蜿蜒曲折地,往天边亮去。
&ldo;艽艽。&rdo;陈皮哑声叫道。
秦艽茫然地睁开眼,立时望进了陈皮的眼里,又是熟悉的眼神,让人心惊肉跳的眼神,秦艽现在算是知道这眼神的含义了。过去还傻傻地以为那是催债的凶恶眼神,根本就是饿极的眼神。
陈皮看见的是一眼潋滟,就像是恍然间春天到了,梨花、樱花、桃花、荷花、梅花全都闹嚷嚷地挤在一处开得乱颤……陈皮已经管不了梅花是不是春天开的,更管不了荷花是不是开在树上的,他只知道就算现在秦艽一把刀插进他的胸口,他也值了。
秦艽知道自己渴望着什么,只要那人是陈皮,她就心里痒苏苏地想要更多,可是在她胸前的那一只手突然撤了出去,笼在她身上的那处热源也翻身离开,火急火燎地冲出门去,不多时就听见外面哗啦啦一片水声。
没了热源,秦艽不禁打了个寒颤,神志才猛然清明起来,想着前几秒自己还在那人身下哼出那么羞人的声音……秦艽颤着手将旁边的被子扯过来,蒙头盖脸地躲进了被窝。
第二日,陈皮自然不能闲在家里,得出去找个挣钱的法子。于是早早地起了床,挑了水劈了柴,又去外边大街上挑了家最热闹的早点铺,排了好一半晌的队才带回来几个包子。回来一看,秦艽果然睡得还熟,可包子冷了会腻,待会儿又得怪陈皮不叫她起床了。
秦艽被空调惯坏了,如今十分怕热,被子早踢到一旁,半挂在床边,将掉未掉。陈皮一见,习惯性地捞起盖在秦艽肚子上,怕她着凉。
确实有些热,秦艽的小脸红扑扑的,也不知翻来滚去多少次,脸上乱七八糟的是她被汗水打湿的长发,黏腻腻地纠结缠绕在他俩的被褥里,身上的衣服经过一夜折腾,早已皱巴巴的,衣袖滑落,露出了柔弱易折的锁骨和小小巧巧的肩膀。
她的睡衣是她自个儿拿着剪刀乱裁的,没有袖子,裙摆短,胸前也低,最是清凉。
陈皮的眼睛轻轻飘过她胸前的雪白,终于还是想起正事,俯下身将她捞起,抚开那些恼人的头发,揪揪脸:&ldo;快起来了。&rdo;
日头也高了,秦艽睡得早,现在应该醒了三分,不过懒,赖床,这么一揪,醒了八九分,迷迷糊糊地就开始发脾气:&ldo;你好烦啊……&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