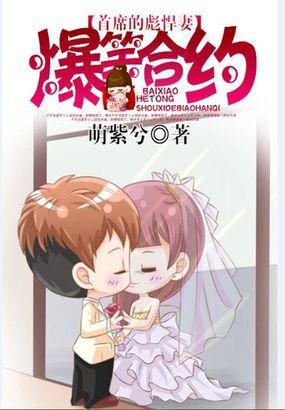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金闺春浓古文学 > 第一百零七章 与你何干(第1页)
第一百零七章 与你何干(第1页)
魏侍这句话刚出口时毓秀甚至有些想笑,她觉这人实在过分狂妄。
“我到不知魏渊是给自己找个了仆人还是给自己找了个爹,难不成他连想找个于自己共度一生的人都要先请示过魏使臣的意思才行吗?”说到这儿毓秀面上有些嘲讽,“若真的是这样,依着毓秀来看,这辽国的皇子不做也罢。”
“钟姑娘不必和我如此大动干戈”,魏侍却不因为她的话而生气,“我确实不喜钟姑娘,可此言却是为你们俩都好。钟姑娘既然承诺不聊殿下什么,不如痛痛快快撒手,免得将二人都耽搁了。”他心里清楚的很,倘若面前这姑娘有丝毫的松口,哪怕他魏侍使尽全身的力气,恐怕也带不走殿下。
他整个魂都牵在了面前人身上。
“你是为了什么,你我都心知肚明。”毓秀并不想和他多说,“还请使臣不要再行干扰,毓秀与你并没有什么事可以商议。告辞了。”
“钟姑娘!”魏侍叫住她,“难不成你就真的如此冷心冷肺吗?”
“殿下为你做了多少的事情,你不是不清楚,你可知他在这里白白耽误一天,便是失去了一个登上皇座的机会。你知道那机会有多难得吗?那是殿下的母亲用命换回来的!”魏侍越说越激动,又看着毓秀,“他一个辽人的混血,若不摆正了身份,凭什么在楚地生存。”
“他现在是锦衣卫都指挥使,可钟姑娘有没有想过,他这辈子也只能是个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看着毓秀,“锦衣卫是什么活姑娘心知肚明,说的是天子近臣,可若说的难听些便是皇帝身边的一条走狗。这样一条走狗倘若失了宠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若有朝一日楚昭登上了帝位,会不会为难这个曾经阻碍他登上皇位的人。”
“魏侍今日所言,皆出于真心。”他道,“姑娘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念着殿下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的份上,好好劝着他回辽吧。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大好前程。”
毓秀抿了抿唇,“那是他的事情,你应该去劝他。”
她心知魏渊回辽是他最好的选择,可若她亲去跟他说,便好似她将魏渊亲手推开一样。她做不到——可又如同魏侍口中所言,都指挥使并不是什么好职位,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实际上却是个得罪人的活计。他本身在楚朝地位就尴尬,长此以往他怎么办?
“我若劝的动就不会来找姑娘。”
“使臣别再来找我了,我的想法你应该看的出来。”毓秀没看他,径直伤了马车。魏侍本来想拦,却无意间看见她脸上慌乱的神思,心中便有了想法,踱步慢了下来,只等马车轱辘开始慢悠悠转了起来。
“我知姑娘口硬心软,只希望你能早日想通。辽人的朝廷不似楚朝这边温和,明证暗夺都在地下,那里真正是在刀锋上过日子。殿下一日不回去接收属于他的势力,他在楚朝便越发的危险。”
那马车没有丝毫缓慢的停留,魏侍却知道她已经把她的话听在了心里。
他虽然不喜这钟家姑娘,却也不得不承认她对殿下并不坏,只可惜两人无论从身份还是各方面都不适合。殿下对她太过关心,太好,只这一点魏侍就不会让两个人在一起。她势必会成为他的软肋——而魏渊,他是辽人的殿下,他知道倘若自家殿下真的有心,他会是辽人的皇。
为君主者,最忌讳的就是软肋。
——
毓秀早上离的府,晚上府时天已经全都暗了。
外头正门闭着,今儿一大早城内的京畿衙门里就满城的张榜,说昭王府出了偷儿,让满城戒严,又封锁了所有的药铺子。她今日出的后门也没旁人发现,自也不晓得她去了魏侍那里。
就算被人发现也没旁的了不起的,楚昭再聪明的脑袋怕也猜不出魏渊的身份。毕竟他的身份在上辈子都只是一个谜团,她自去了魏使那里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一个辽人的使臣,管楚国的贪污舞弊做甚,他便是告发给了楚皇也得不到任何的一官半职。
只是临到了跟头,也并不像节外生枝,便又轻口嘱咐了车夫,让走后门。
——
大周氏深夜还没睡着,温嬷嬷便又给她倒了水,“别再喝茶了,夜里该睡不着了。”
这么多年两人情同母女,也没什么可顾忌的,大周氏便拉着温嬷嬷的手,“我心里不踏实。”从早上一直不踏实到现在,她眉头皱着,又想起早上她跟她说的话,“毓秀这丫头从小就内秀,偏偏心里想法又多。跟她父亲和祖父一个心向,他们还老护着她,有时候我真觉得……”
“老爷和太傅总不会害了小姐,夫人,你别想太多。”温嬷嬷拍了拍她的肩膀,“小姐聪明也是好事儿,况且她貌美又孝顺,如今谁不羡慕夫人生了这么个女儿,比起旁人家里的,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呢?”
大周氏笑笑,“偏生拿这些话来哄着我。要我说啊,宁愿她比旁的姑娘普通一些,只要日子过的太平就好。”
温嬷嬷轻柔的给她盖上了披肩,“天底下的母亲也总是这么想的。”温嬷嬷年轻的时候是伺候大周氏母亲的,到后来大周氏的时候,因为得大周氏喜爱,便又给她做了陪嫁一路到了钟府,“当年老夫人怀了双胎,满个府里等你们姐两出来得时候都夸呢,偏偏她总忧愁着,和今日你说的话一模一样。”
想起母亲,大周氏唇角弯弯,“母亲死的早,但我记得,她是个极为温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