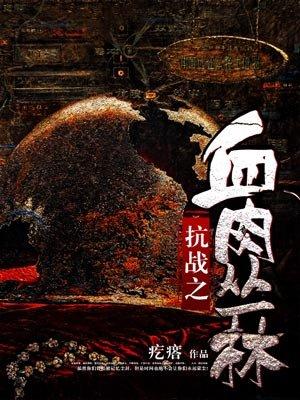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杀了我拯救我翻译 > 第36章(第2页)
第36章(第2页)
然而脚步就是迈不动,眼睛死死盯着小小的婴儿,再看一眼吧,反正以后都见不到了。
最后瓦解掉何云越的决心的是冉竹的一个笑,小小的婴儿无知无觉,偏偏就朝着何云越的方向笑了一下,咧开嘴,天真无邪。
只是个巧合,但是何云越相信这是天意,她留了下来。
在电话亭里拨号,号码烂熟于心,手却迟迟不敢动,最后心中默默想了几遍躺在保温箱中的冉竹,手还是按下去了。
熟悉的声音响起,何云芬开口,&ldo;妈,我是云越。&rdo;
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而还是没挂电话,何云越看着电话亭玻璃窗里映照出自己的脸,面上憔悴,头发蓬乱,眼睛里都是血丝‐‐一个疯女人的形象。
&ldo;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rdo;那头的嘲讽刚开了头,何云越就将它打断。
&ldo;妈你借我点钱吧,我会还你的。&rdo;何云越重重地讲着借,仿佛要打消妈妈的怀疑,也要打消自己的怀疑,心中很清楚,自己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而未来的日子像一片沼泽,只会把人往下拉,看不见出头之日。
&ldo;那男人呢?跑了?&rdo;
何云越不开口。
&ldo;臭丫头,我当初怎么告诫你的,不要信男人的话,好好嫁个好人家就够了,你偏不听,死活要跟人走,现在好了,被骗了,开心了,那王八蛋,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rdo;电话那头骂声无休无止。
&ldo;妈我生孩子了,她还躺在医院呢。&rdo;何云越只用了一句话就终止了对话。
那头的沉默像黑洞,吸空了何云越所有的自尊,苦苦维持着一切,希望可以扬眉吐气,最后不过是印证了老人言,还是要灰头土脸的回去,像个笑话,只供人娱乐。
&ldo;你的卡号多少?&rdo;
何云越回答了,听见那头继续说,
&ldo;钱不用还了,你以后别打电话来了,也别回来了,我就当死了个女儿。&rdo;
电话挂断,何云越在原地站了很久,走出电话亭时只是觉得阳光刺眼地狠,眼前一片模糊。
抱着冉竹出院时,一个人在医院外站着,看着车子来来去去,四面都是路,四面都没有她的路,每一个方向都是绝境。
最后还是坐上了回乡的车。
厚着脸皮,顶着众人讥诮的目光,装作若无其事,越是被轻视,越是要骄傲,背地里的伤痕就自己一个人舔舐。
冉竹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何云越没有时间来照顾他,她白天要上十二个小时的班,厂房里机器轰鸣,喧嚣得像个孤岛,莫名想起了那男人给她讲的诗,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然而抬起眼,连天空也不曾看见,厂房的天花板极高,黑压压的,像囚笼,何云越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走不出了。
回到家,冉竹通常都和大狗一起玩,一人一狗,坐在地上,宋大宝对大狗讲故事,讲今天发生的趣事,讲电视里放了什么。
何云越冷漠地走过,&ldo;冉竹,大狗不是人,你对它讲什么,它都听不懂的,你要不要出去和小朋友一起玩。&rdo;
冉竹一下子就沉默了,坐在地上,摆弄着玩具,待到何云越走过,仍旧和大黄讲话,声音低低地,&ldo;大黄,我今天看见电视,他们讲你的祖先是狼,你知道什么是狼吗……&rdo;
后面的何云越没有听见,她已经关上了门,躺在床上,明天,明天后又是明天,生活重复着,永无止境。
她沉沉睡去。
☆、第二十七章幻象重叠
冉竹冷眼旁观着一切,像是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她记得那条狗,最后被车撞死了,那天也是大雨,自己在雨中的马路上坐了一晚上,最后被一个巴掌扇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