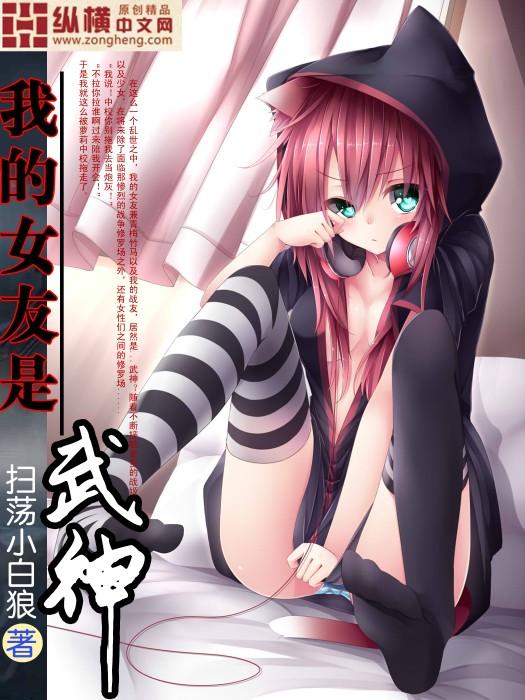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绝色倾城2非我情迷女主免费阅读 > 第56章(第2页)
第56章(第2页)
他叹了口气,把脸贴在我胸口上,&ldo;你还是不愿意说。可是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能感觉到,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只是不愿意承认。小夏,你相信我,无论我曾经让你失去过什么,我都不是存心的,你不要因为那些事情记恨我……&rdo;他的声音慢慢小了,大约是困了,我像哄婴儿一样拍着他的背,低声问:&ldo;你觉得你能让我失去什么?&rdo;
&ldo;我不知道。可能是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因为我霸占了你,逼得你们分开了,你才一直怨我,不愿意承认你喜欢我,是不是这样?&rdo;
我笑了起来,&ldo;青梅竹马的恋人?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rdo;
他也笑了笑,好像困意更深,含糊地小声嘀咕着:&ldo;不管是不是,我都向你道歉,你别再恨我了。你已经惩罚了我三年,我有感觉的。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真的能感觉到,这三年,你虽然躺在我身边,可是你心里一直因为某件事怨恨我。如果你不是知道我有病,你不会回来,也不会对我这么好。可是,小夏,人活这一辈子,不可能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有时候对别人的一些连带的伤害,或许是我们自己都无法预料的。如果你觉得我哪儿做得不好,你就告诉我,我一定会改,只要你开口……&rdo;
他握住我的手,在我指尖上亲了一下,&ldo;几个月之前,我还有勇气让你离开,可是现在真的不行。我已经不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你做得太好,我又没那么坚强,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小夏,其实你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把我们分得这么清楚,让你向我要求点什么,就这么难吗?后来我明白了,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希望我们是平等的,你要的是一个平等的态度。你从来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样你才能游刃有余,才能更自由。可是,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因为我早就爱上了你,可你呢?你的心又在哪儿?&rdo;
他揉了揉我的辱房,好像这样就能把厚厚的胸壁弄透明了一样。我感到胸口上有点凉意,好像是文昭的泪水,转瞬即逝,却凉得我心都疼了。
我很想开口跟他说点什么,哪怕只有一句也好,可是动了动嘴唇,依旧是徒劳。
&ldo;我不管了,当初是你自己回头的,我没逼过你,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不认。&rdo;他的脑袋在我怀里蹭了蹭,似乎在找一个舒服的位置,&ldo;我们要一起生儿育女,最好是多生几个男孩,等我老了,可以把家里的事业交给他们打理。我就可以带着你,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岁月太长,我不敢保证不让你受半点委屈,但我会努力对你好,用一辈子的时间补偿你的遗憾,让你幸福……&rdo;
我的心跳慢了一拍,看了看他,或许就是现在,&ldo;文昭,我想跟你说一件事……&rdo;
没人应我,原来他已经趴在我怀里睡着了,一只爪子还没忘了压在我胸口上。
我无奈地将他推到一边,他醒了一下,自己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被子只盖了一半,这次倒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对未来有无尽的期待,连睡觉都能笑出声来。
我帮他把被子盖好,看着他毫无防备的脸,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等到他的鼾声响起,我自己反而没有睡意了,想到浴室冲一个澡,一下床才发现两条腿酸疼得厉害,有什么东西从腿间流了出来。
我愣了一下,抽出床头的纸巾擦了几下,将废纸扔进垃圾桶里。
洗过澡之后就更不想睡了,我坐在书房的电脑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避孕药。这盒&ldo;毓婷&rdo;还是凌靖在医院买给我的,那时候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很多人还没有认清,很多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
我拿着那个盒子,理智告诉我应该打开它,吃下去。从三年前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难道,真的要给他生儿育女吗?
可真正动手的时候,眼前出现的却是文昭提到孩子时那副既满足又憧憬的表情。我将避孕药扔回抽屉里,靠在椅背上,看着落地窗外的夜空。
刚才跟凌靖说得很硬气,可是到了真正面对的时候,心中依旧彷徨。我该怎么跟文昭开口?说出来之后,结果又会怎么样?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又该如何面对?
我不敢想,真的不敢想,每次想到这一层,就感到自己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吞没了。
三年时间,我曾经为我们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但任何一种可能的结局,似乎都是&ldo;左右为难,穷途末路&rdo;。
腿有点酸,我将它们搭在电脑桌上,看着脚上那串铃铛,这件礼物是文昭亲手做的,又亲手为我戴上,他在众人面前俯身的姿态,让这件原本普通的礼物变得意义非凡。
我忍不住想,这件事如果让韩棠知道了,大概又会嘲笑文昭没出息。他不止一次找各种机会冷嘲热讽,说文昭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对我太纵容。
文昭从来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那个不依不饶又不可一世的好友说:&ldo;她跟夏荷不一样,这些年从来都不是我管她,是她在包容我。&rdo;
我默默看着那串铃铛,它的确来源于一部电影,可那部电影文昭只看了一眼,就匆匆出门了,所以他并不知道,那是一部讲述一座古老城池的百姓被侵略者残忍屠杀的电影。
戴着那串铃铛的女人是秦淮河边的ji女,她们的历史跟那座城池一样古老。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当头,她和其他九十九个女人为安全区的难民换来了食物、棉衣和过冬的煤,代价是侵略者的士兵‐‐那些形同禽兽的男子可以任意享用她们的身体,时间为三周,去了一百人,最后活着回来的不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