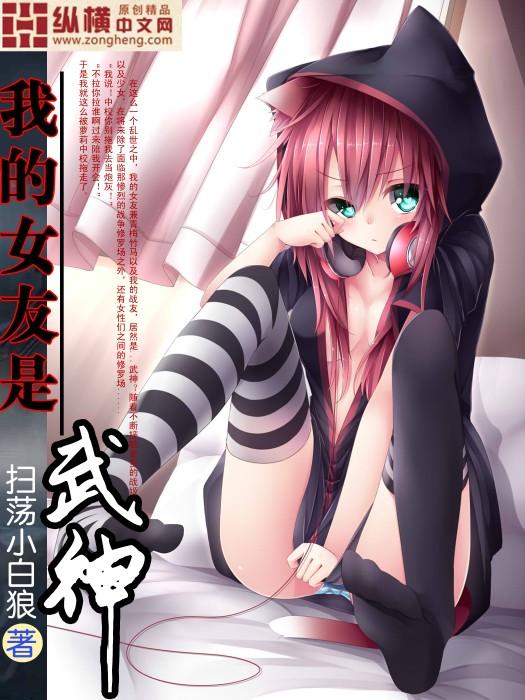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绝色倾城2非我情迷女主免费阅读 > 第131章(第2页)
第131章(第2页)
&ldo;他那样害你,岂止是劣根,简直就是无耻。&rdo;恕一不屑地说。
我笑了一声,抱着膝盖又想睡,&ldo;谁没害过我?直接的,间接的,我爱的,我恨的,害过我的人太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计较不过来了。到了最后,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我觉得自己有点惨,却连个可以责怪的人都找不到。你说多可笑?所以,我谁也不怨,路是自己走的,我就怨自己。&rdo;
恕一哑了哑嗓子,悲悯地望着我,&ldo;小夏,别这么说。堂哥说了,以后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会再干涉,你自由了。&rdo;
我含笑看着他,虚弱地想,你究竟知不知道,你堂哥这次让你陪我回来,到底来做什么?
看着他诚恳的眼神,我发现,他真的不知道。
&ldo;外面好像下雪了。&rdo;恕一站起来,绕过桌子,贴着玻璃窗,向外看了看。
我望向窗外,真的下雪了,北风潇潇,卷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飘向无穷无尽的黑暗,凛冽如刀。我恍恍惚惚地看着,不知道地狱,是不是这样的光景?
可是,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地狱?没有地狱,自然也不会有天堂,没有前世,也就没有来生。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相信,人死了就是死了。死亡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再有痛苦,不会再有记忆,不会再让一个怎么都死不了的人活得生不如死,也让那些生无可恋的人,有了去处。
&ldo;看来,我们要在山上过一夜,我一会儿去跟老板说一下。&rdo;恕一对我说。
一阵电话铃声,是恕一的手机。他接了起来,几秒钟后,看了看我,对着话筒说:&ldo;是的,在这儿,你要跟她说话吗?&rdo;
恕一把电话递给我,我接过来之后,看了他一眼,他知趣地走了出去,留出私密的空间给我,还有远在港岛的韩棠。
我把电话放在耳边,对面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音。
我趴在窗边,迷迷糊糊地推开窗子,凛冽的北风呼地吹进来,带着几片白色的雪花,砸在我脸上,又凉又冷,就像文昭的泪水。
而韩棠,这个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出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男人。我一直记得,六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漫天的火光中向我走来,像童话里的超级英雄,救我走出那片水深火热。
六年岁月,他给了我最安稳的日子,最温暖的时光,最顽强的意志,最坚定的希望。
此刻的他在电话的另外一端静默着,我们中间隔着千里土地,生死两端,谁都没说话,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是啊,让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太熟悉了,擂台上一个会意的眼神,一个浅浅的微笑,一个小小的手势,不需要多余的语言,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既然如此了解,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坚持了这么久,努力了这么久,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想法,有些话,我说不出口,说出来也不会被人理解,理解了也会被千夫所指,那是我的罪过,我一生最大的负累。可是我知道,你都懂。
所以你怎么会不明白?文昭和小柔,他们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两个人,我失去了一个,怎么也要保住另外一个,这才是我活下去的动力。你说你明白我的痛苦,你知道我活着比死更难受,你知道我当初将一切揭穿,真正想要惩罚的人不是文昭,而是我自己。总要有人为小柔负责,他不行,就只能是我。
可是你又是否理解,我扛下一切,不是想要那个人偷生,而是希望他能得到新生。我几乎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他的悔悟,是希望他能明白什么叫作失去,是希望他能更加尊重生命。
我知道,没有真相可以被掩盖,总会有人为谎言付出代价。可是那些苦我已经吃了,罪我已经扛了,我不需要任何人再为我的痛苦负责,你又懂不懂?
我是一个俗人,没什么太高尚的追求,我做尽了一切,只是希望他能活着,好好活着。是你告诉我,他过得很好。我信任你,就真的以为是很好。我以为自己可以放下一切,开始新的生活,没想到,连你都骗我。
骗我不要紧,可是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你至少……应该在睡我之前,把文昭的事跟我交代一下,至少跟我打个招呼。那样,我现在就不会这么难受,有苦说不出来的难受。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我努力睁开眼,眼前是一望无尽的深谷,天与地模糊了界限,乌云密布,黑暗滚滚而来,霎时吞没了我。
我勉强拿着电话,心里有千言无语,可话到嘴边,已经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