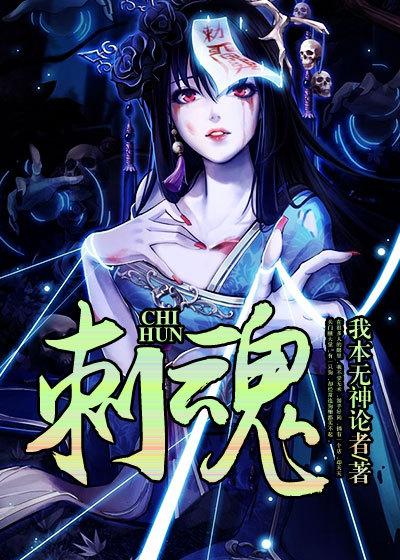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兽王传奇战争之鼓 > 第一百三十二章 世间恶臭(第1页)
第一百三十二章 世间恶臭(第1页)
毛无邪闪身避开蛇头,心中却惊疑不定:自己的应变,怎么慢了半拍?记性也变得不佳,明明见过这种毒蛇,竟然一时想不起它的名字?莫不是这恶臭竟带有毒性,让自己不知不觉着了道儿?
运内功一试,果然内息不畅!幸而野兽邪毒与“兽五行”真气所化的“兽王神功”乃是天下剧毒的克星,这毒性又毫不猛烈,以毛无邪如今的功力,转眼之间已将小毒从毛孔中逼出体外,头脑恢复了清醒。这时候,他才记起了是什么毒蛇,那竟是剧毒无比的银环蛇,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有言:“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所说的正是这玩意儿!
再看那只臭鼬鼠,正叼着无头的蛇身,撕咬啃食,吃得不亦乐乎。没了头的蛇也不得便死,扭动挣扎不休,却全然逃不出这异种臭鼬鼠的掌握。再看这异兽的四肢,前足爪长,后足爪短,前脚上的利爪竟有寸许长短,锋利如刃,难怪一挥之下,将那条剧毒的银环蛇一分为二。
小小一只臭鼬鼠,竟也懂得扮猪吃老虎?毛无邪小觑之心尽去,气运周身,凝神戒备。以他对钟剑圣的信任,本不该大意如此,莫非那恶臭,竟能不知不觉扭转了他的心智?若当真如此,这臭鼬鼠果然极不好对付。
若论强悍凶狠,这臭鼬鼠或许能胜过黑狼之类,却未必斗得过恐怖鸟、雪人与双头兽诸般罕见的怪物。凭这点本事便让七兄弟也不敢招惹,自是万无此理。须知那钟三钟九五是用毒高手,这恶臭气味的毒性轻微,远不足以致命,哪里难得倒他?看这厮如此满不在乎,必有更厉害的招数尚未使出。适才一爪击杀毒蛇,将蛇头抛向毛无邪面门,用力极巧,竟有暗器高手风范,是有意还是无意?毛无邪心念一动,随手折了一根树枝,运起内力,甩手向那臭鼬鼠掷去。当年毛无邪的师弟乐苇喜爱暗器,造诣甚高,又与毛无邪交情最好,日常切磋频繁,这暗器功夫多少也让毛无邪学了些准头。
那臭鼬鼠听得风声,不慌不忙,脑袋一甩,叼在嘴边的半截蛇身扬起,将飞来的树枝打偏,擦着耳朵上的绒毛飞了过去。这一着用力恰到好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难得的是纯出自然,看不出是刻意之举。
好家伙,还真懂武功?毛无邪越发不敢大意。其实这臭鼬鼠再厉害,焉能敌得过兽王的“五行归一,一家独大”?可毛无邪来找这属土异兽,乃是为了吸纳地灵之气,收集“兽五行”中的一行,若宿主死亡,灵性尽失,哪里还有五行之气可供吸纳?眼见这臭鼬鼠极富灵智,体内土气必不寻常,毛无邪更是志在必得,绝不肯痛下杀手。
如何与这灵兽好好商量,说服它借灵气一用?毛无邪苦苦思忖,不由自主缓缓踏前了一步。那臭鼬鼠还是只顾大嚼着毒蛇,眼睛虽盯着毛无邪不放,却无一丝惧意。毛无邪极慢极慢地又走近了一步,臭鼬鼠却似不大高兴,放下嘴里的美餐,脑袋贴地,尾巴高高翘起,前爪在地面上轻轻跺着。
看来主人对来客并无好感,走远些晃悠无妨,相互扔点东西也不伤和气,却不许相距过近。毛无邪也顿住了脚步,一人一鼬相距仅有一丈,他盘算着施展“有影无踪”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臭鼬鼠击晕,先行生擒活捉,再想法子化敌为友。然而这异兽倒也不蠢,竟将脑袋放得如此之低,毛无邪若不下蹲弯腰,伸手够它不着,下蹲弯腰,身法却欠了灵便,用脚踢其头自然能又快又准,但脚上劲道远没有手上收放自如,一不小心,将那小脑袋踢得稀烂,那可事与愿违。
臭鼬鼠虽伶俐,终是野兽,见毛无邪半晌仍未知趣走开,按捺不住,忽然一个转身,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一条水箭激射毛无邪面门,其准无比。
毛无邪伸掌一挡,只觉掌心粘糊糊的,接着一阵入骨奇痒,看来这并非尿水,而是毒液!毛无邪连忙深吸一口气,欲运功逼毒,不料一股生平从未闻过的浓烈臭气涌进鼻腔,较腐尸、大粪、瘴气之类不知臭了多少倍,脑中一时热血乱撞,刺痛难当,一阵头晕目眩,两耳轰鸣,说不出有多难受。
臭鼬鼠的恶臭毒液,毒性也不甚强,但其臭味,实是天下无双,常人全然无可抵御,而臭气之浓,甚至两里外亦可闻得到。洞府中的臭鼬鼠,更是天外神仙做过手脚的异种,除心智极高、凶猛异常之外,体内恶臭更是冠绝天下。钟家七兄弟以神仙自居,自视甚高,不招惹臭鼬鼠自然不是惧怕,而是厌憎。便算喜爱驯兽的钟七钟万岁,也知道若活捉豢养臭鼬鼠,别的异兽定然生不如死,因此也懒得来这片林子倒胃口。毛无邪因中了野兽邪毒,半人半兽,嗅觉甚灵,闻这恶臭,一如耳聪者听巨响,夜视者照强光,所受苦楚,更远为剧烈。
然而天地万物与五行相似,相生相克,无论多强悍的猛兽,均有其克星。臭鼬鼠得意洋洋之际,一只高大的巨鸟忽然从林中一跃而出,一口便将它吞了下去。
来者又是一只恐怖鸟。相比海滩上吃海鳄的巨大同类,这只巨鸟小得多,身高仅到常人肩头,但在鸟类之中,也算庞然大物。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臭鼬鼠在这片林子中,可称天不怕地不怕,却唯独惧怕恐怖鸟。寻常恐怖鸟身高一丈有余,在密林中自然缚手缚脚,施展不开,但如同龙生九种,猕猴与山都均是猴子,长相大不相同,恐怖鸟也是如此。今日这别种恐怖鸟身高仅六尺,重一百四五十斤,全身钢针也似的蓝黑色长毛,细密蓬松,坚硬如刺猬身上的刺,头颈无毛,脑袋上一个角冠,看似张开的折扇。两脚粗壮,各有三趾,其中最短的脚趾上,更生有一根五寸长,犹如匕首般的利爪。纵然遇上虎豹,也可开膛破肚,厉害之极。那张巨嘴则与同类一样,大得可怕,臭鼬鼠再怎么说也有十几斤重,竟然只一口,便囫囵吞下。
照说臭鼬鼠的臭液威力无比,强如毛无邪,深吸进一口气味也臭得头晕眼花,恍惚迷糊,寻常猛禽恶兽,自当退避三舍。但这角冠恐怖鸟更生具异相,听觉极其敏锐,却全无嗅觉,鼻子只是呼吸之用,丝毫不懂香臭之别,鲜花大粪,于它都是一般无二。
虽说不畏惧恶臭,密林之中美食众多,恐怖鸟本也不必找臭鼬鼠的麻烦,毕竟对方虽小巧,也是凶兽,且机变百出,聪明绝顶,实在不好对付。然而这臭鼬鼠的肉,偏有一般奇妙处,便是有极强的明目功效,这异种恐怖鸟眼睛不比虎狼夜枭,若一连几日不吞食一只臭鼬鼠,夜晚便如家养的鸡一般,看不见东西。密林之中,没有别的活物有此功效,角冠恐怖鸟不找臭鼬鼠,又去找谁?
只不过,今天这场觅食,角冠恐怖鸟实在找错了地方。那只臭鼬鼠刚进嘴巴,正自下咽,忽然身后掌风犹如利刃,角冠恐怖鸟未及回头,毛无邪的掌刀已然横劈而至。下一刻,角冠恐怖鸟也如同那条银环蛇一般,脑袋离体,飞起老高。吞咽未停,却将那臭鼬鼠的小脑袋从脖子处的断口挤了出来。
毛无邪毕竟功力深厚,虽被恶臭折磨得痛苦不堪,也强打精神,杀了这不速之客。手掌依旧极痒,毛无邪运起五行真气中的烈焰之气,掌心片刻间热如火炉,臭液在高温之下,不久便焦黑一片,成了另一股气味,虽说也极不好闻,总比原先好得太多。
角冠恐怖鸟的脑袋早已落地,和脑袋一起摔得七荤八素的臭鼬鼠,也从脖颈的断口处钻了出来,蹲坐于地,也不逃逸,歪着头打量毛无邪,尾巴依然摇来晃去,乌溜溜的眼睛里,闪烁着荧荧碧光。
毛无邪缓缓坐下,屏住呼吸,暗自运气平复五脏六腑中的痉挛。适才的极度恶臭,让他肠胃几乎绞作一团,胆汁胃液都涌上了喉头,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张开嘴巴,“哇”地吐了一地,眼泪鼻涕,流得一塌糊涂。
十余日之前,毛无邪尝过了世间极辣,以为世上痛苦,莫过于此。不料今晚竟又闻得天下极臭,当真刻骨铭心,一生难忘。这一吐,竟然无休无止,将肚子里的东西吐了个一干二净,还在不断干呕。毛无邪这时也顾不上与那刚逃得性命的臭鼬鼠拉交情,发足狂奔到一处小溪边,喝了一肚子水,又吐将出来,再喝再吐,再吐再喝,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才缓过一口气来。只觉全身上下,没了半丝气力,瘫坐在地,一根手指也不想动弹。
抬起头来,那臭鼬鼠竟不知何时坐在了对岸,前爪捧着那半条银环蛇,吃得正香。
这厮胃口倒好,难怪肥胖若此。毛无邪心里暗骂,却已懒得与这臭鼬鼠计较许多,仰天躺倒,闭目养神。他知道,自己往后的几天,是别想吃得下什么东西了,那恶臭于他,竟比那“化尸蓝蛙”可怕得多。
耳听一连串轻微脚步声响起,似有不少野兽从林中奔出,集结在一处,却不闻一丝嘈杂。毛无邪好奇心起,抬起头时,溪流对岸已然不是一只臭鼬鼠,而是数百只。均是黑白相间的皮毛,纹理各异,但两眼间均有一条狭长的白纹,夜色中依然抢眼。毛无邪一个哆嗦,如今的他,见了黑色与白色搅合在一起,心头都不由自主发瘆。奇怪的是,这数百只臭鼬鼠都规规矩矩蹲坐在第一只臭鼬鼠的身后,不声不响,只不停打量着半死不活的毛无邪,看得他全身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