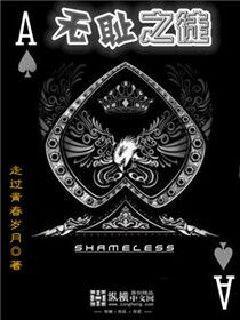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霸道总裁独宠文无虐 > 56结婚第二天(第1页)
56结婚第二天(第1页)
池晏直直地注视着门口。
这话嚷得石破天惊,使得屋内转入寂静。阮绵的拳头因为羞恼而捏紧,心脏忐忑乱跳。
池晏目光微动。
“……”
这番沉默的对峙从小狗视角来看,就像在审视他的真假,阮绵原本憋在心头的火气蹿起三层高,心想着“我是为了谁才回来的!要不是你露出那种眼神我也不至于——”
然而话到了嘴边。
“楼……楼下买的。”阮绵气虚地伸出手,指着刚才丢到床上的东西,“阿嬷说可以吃。”
那是一袋干制红枣,暗红大个,整整齐齐地码在塑封袋里,看起来倒像是来慰问病人的。
池晏看着他。
阮绵登时气更虚了,“……我问了,她说这个时候可以吃红枣。”
池晏:“什么?”
阮绵支吾道:“就是……这个时候!”
池晏沉默思索着是小型犬类有自己的语言逻辑,还是阮绵的语言组织能力出现了问题,说话含糊不清自带漏字屏蔽系统。
阮绵被他看笨蛋小狗的眼神盯得恼怒无比,冲上去拎起那袋红枣,“阿嬷说——结婚第二天都可以吃这个的!”
话音刚落,阮绵的脸在池晏肉眼可见的状态下,陡然涨红成小番茄。
池晏掀起眼,直勾勾的。
阮绵:“……”
“没说我们结婚!”阮绵羞恼万分地捂住嘴,从指缝间憋出几个字,声音唔唔的,“就是这个意思,你意会一下不行吗?!”
他这个人越理亏心虚的时候话越多,像只被人拎住了脖子提起来的小狗,因为腿短踹不到人,只能胡乱扑腾着嗷嗷乱叫,甚至欲盖弥彰地张嘴轻咬几下。
“那叫,”池晏冷不丁道:“??。”
阮绵:“……”
阮绵“啊”地哀嚎一声,捂住脸不想跟他说话了。
之前在楼下杂货铺的婆婆面前,锯了嘴的葫芦阮绵僵硬了一分钟都没好意思说出这个词。婆婆以为他有什么难言之隐,耐心又循循善诱地问,阮绵被问得受不住,将“??”两个字的意思延伸为一段话,又七扭八扭地拧成“结婚第二天”五个字,硬着头皮挤出来。
……希望别人听出他本意,又不希望别人听出他本意。
现在被池晏拆穿,阮绵只想纵身一跃,融入户城江水的怀抱,忘却这些前尘杂事。
红枣袋被翻动发出“唰啦”的声响,池晏托在手里看了两秒,随手放到床头柜上。
阮绵见他并未拒绝,忽然欲言又止。
这很反常,池晏往日里总喜欢他的挑刺,几乎总是恶意地踩在他的羞耻心底线上。现在却安安静静,垂着眼受到了莫大的伤害,不是很想理他的样子。
比起这幅模样,阮绵宁可他打自己、骂自己,也好过这般受到了??而沉默的样子,仿佛对于自己愿意负责这事不太相信,冷冷淡淡,心灰意冷。
阮绵心脏忽地被揪了一下,刺痛得厉害。
他站在那里急得抓耳挠腮,将本就没打理的头发挠得更是蓬蓬乱。棉花团小狗的棉花一点都不服帖,衬着蹬错的不同款鞋,显得傻里傻气。
阮绵低头才发现自己匆忙中穿错了鞋子,不动声色地抬脚,将脚丫子从池晏的鞋里面抽出来,一点一点地伸向自己的鞋。
“所以呢。”池晏出声道。
阮绵一惊,神经被拉扯着错了位,脚不知该抬起还是放下,僵在那里不敢动,“啊……啊?”
池晏:“不要做无意义的承诺。”
阮绵愣住了,抬起的脚也愣住了。
下一秒,阮绵反应过来,怒道:“我是认真的!”
池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