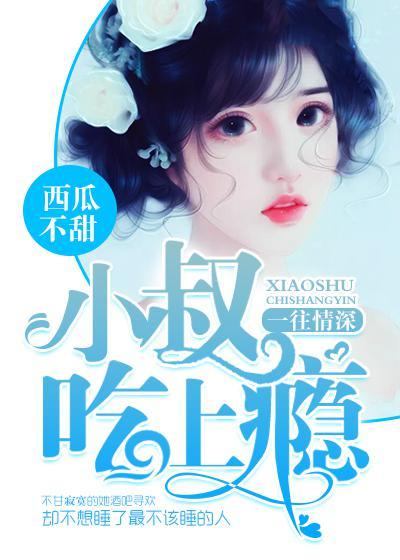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农门有喜宰辅相公宠妻日常 > 第57章 赵氏的小傲娇(第1页)
第57章 赵氏的小傲娇(第1页)
无论陈常君乐不乐意这么早起来,一家人都不介意把他架着同行去镇上。
除了不能下地的陈常坪,一家人说笑着往村外走。
出村的小路上零零散散都是本村人,人影在树影中穿行,点点灯光与星空辉映。
五月初五的月亮犹如韭叶,出行的人都要提着着灯笼,即便不怕走夜路,也得让人知道自己家这资本。
陈家提着的这三盏灯笼格外惹人注目。
莫宛央跟陈常君坦言,从前一直生活在京城的她,也不曾见过过如此精美的灯笼。
她指着小秋那盏道:
“都说‘花灯微透’,我见这几盏的灯纱波如蝉翼,但粗糙一点的手去触碰又不会令其抽丝,不知是哪里的工艺,如此令人叹为观止。”
小秋抬头道:“还有香味呢。”
陈常君若是有所思、一本正经地回答:“大概是外邦的蚕比较会吐丝。就好比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莫宛央被陈常君逗笑。
一家人得意地走在路上,陈常君也不例外,将“肤浅”“炫耀”几个词展现地淋漓尽致。
毕竟,他只有九岁。
经过自家水田时,陈源要其余人在路上等一会让,特意提花灯去查看一番,返回后正是后面几个村民赶上来的时候。
陈源提高嗓门感叹:
“新种的粳米都有冒头的了,今年肯定不用卖地过冬了。明儿我得到地里看着,可别让雀儿把嫩苗给我啄了。”
赵氏在一旁附和:
“若不薅掉原来的籼米苗,粳米也没地方种啊。真羡慕一辈子只能吃籼米的,就不用受这种晚稻的苦。”
夫妻俩一唱一和,赶上来的人都听个真真切切。
一家人就掺和在其他人群中前进,别人快,陈家就快;别人慢,陈家人就慢,“粳米”、“良田”、“小当家”夸个不停。
人群里有人不屑地“哼”着。
赵氏拉着小秋,提着花灯就左晃右晃,一会儿去夸人家花灯“还是老物件瞧着舒坦”,一会儿夸赞“这灯笼就是一点都不刺眼,不像我家的,晃地人眼花”,一会儿又说“还是你们会过,蜡烛跟小手指一样细”。
这就是欠儿蹬。
不过陈常君也不比他娘好哪儿去,痞子就算开窍,也得像个九岁的孩子,必须看热闹不嫌事大。
在陈常君和赵氏几番“不经意”地对话下,很快就听到不懂事的孩童哇哇哭开,非要一样的花灯不可。
“又不是中秋节,拿个花灯显摆什么?!”终于有妇人忍不住,低声呵斥。
大伙儿目光集中过去,原是村里豆腐坊的钱家媳妇。
赵氏瞥了眼,哼笑道:“呦,好像七夕、中秋你就拿得出来似的。”
“哼,不就一个破灯吗!我要是没记错,上次逛草市时下大雨,也不知哪个连把伞都没有,浇得跟个水鬼似的!”
“呦,那是我喜欢淋雨,可不代表我没有伞。”赵氏扭着腰,浑身上下散发着小傲娇。
说着,赵氏从腰间的口袋里摸出黑科技五折小洋伞,啪地一声撑开,得意地抱起小秋:“秋儿啊,娘这伞不光能遮雨,还能遮阳呢,好不好看啊?”
小秋儿哪知道大人之间的斗气,凭借自己单纯的审美观非常干脆地回答:“娘的伞最好看!”
“哼,有些人啊,就是看不得别人好……”赵氏开始阴阳怪气地开口。
陈常君真诚地劝诫赵氏:“娘,别这样……”
“别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