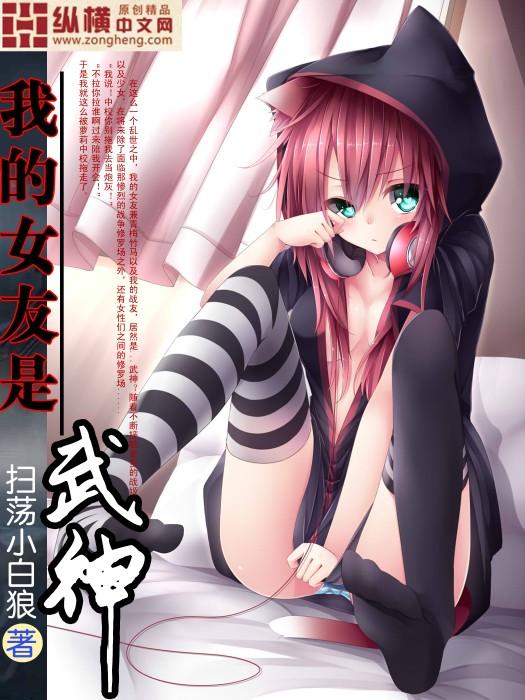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月夜花朝下一句 > 第5章 23(第2页)
第5章 23(第2页)
顾勋朝张冲以眼神示意,张冲便开口问道:“八月初十,子时到卯时,你在身何处做过什么事。”
冯七咽了咽口水,颤声道:“那晚小的见宫内没什么吩咐,就和刘福、周瑾凑在一起玩了几把骰子,一直快到卯时才离开,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啊!”刘福和周瑾便是当晚当值的另外两名太监,张冲知道宫内的小太监聚在一起都爱赌点小钱,虽然有违宫规,却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他思忖一番,又问道:“那你们可曾听到什么异响。”
“确实未听到有什么声响”
“你们那晚是谁赢了钱。”顾勋突然慢悠悠地开口道,声音不大却听得异常清晰。
冯六连忙不假思索地回道:“是刘瑾,本来我先赢了五两银子,他们非不让我走,谁知最后几盘刘瑾手气极好,硬是害我又倒亏了八两。”
“那最后是谁输得最多?”
冯六立即回道:“是刘福,这小子估计把这月的月俸都给输了进去。”
顾勋若有所思地盯着他许久,才道:“好了,你先下去吧。”
冯六如释重负地被带下堂去,其后审问得几人供词与冯六几乎分毫不差,根据他们的供述,当晚冯六、刘福、陈瑾聚在一起玩骰子,因为刘福一直在输钱,为了翻本便不让另两人离开,将赌局拖到将近卯时才结束。另两名太监并未参与,但都全程在一旁观看,偶尔买上几把,从时间来看,确实个个都无可疑之处。偏偏他们都耽于博钱,都未留意外面有何奇怪声响。
顾勋望着眼前的供词,问一旁的张冲道:“你觉得这供词有何问题?”
张冲道:“根据这些供词,在陈安被杀又被吊起来的这段时间,确实无人有犯案可能。莫非真有外人潜入杀了陈安。”
顾勋摇了摇头,道:“即使是一流的武功高手,也不可能在禁城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的手指在供词上扣了扣,道:“这些供词确实是毫无破绽滴水不漏,只可惜,它们做大的问题就是太过滴水不漏。”
他唇角挂了抹浅笑,又道:“五个人,五张嘴,对当晚的事实供述却不差分毫。几日前发生得事,每个人都能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每一个细节都说得清晰无比,这本身就不合常理。而且按他们所言,刘福当晚输了整月的俸禄,而当他说到此处时连语调都未变过分毫,好似在陈诉一件无关紧要之事,你说这是不是非常奇怪。”
“大人的意思是,他们所言极可能都是谎话,为了掩盖那晚的真相。可他们为什么要说谎来包庇凶手呢?”
顾勋抬头望了他一眼,语声铮铮道:“因为他们五个,都是凶手!所以事先能套好供词,互相包庇,互相掩护。”
张冲吓了一跳,皱起眉头道:“这五人与陈安到底有何仇恨,竟能一齐下手将他杀害,还要在他死后把尸首悬在殿外示众!”
顾勋道:“说起此处,又是另一个极不合理的地方。宫内禁卫森严,每隔一个时辰都会有侍卫巡视,杀了人自然是立即埋尸最为隐蔽妥当。可他们五人却要冒着随时被发现的危险,费劲心力将尸首悬上屋檐,招摇示众。我实在想不出是何道理。”
“莫非他们对陈安有彻骨之恨,宁愿冒着随时被捉到的危险,也要让他曝尸在外,”
“那尸首虽然面目可怖、腹上还被破了洞,但他身上的衣服却平整完好,可见是死后才被穿上的,尸首脚上还穿上了一双白靴。根据民间传言,死去得人要穿上鞋子才能找到去黄泉的路,不然就会变成孤魂野鬼流落在外。那凶手如果真得那么恨陈安,又为何在杀了他以后要为他穿上干净的新衣,还为他想得如此周到,生怕他变成孤魂野鬼。”
张冲听他一说,也觉得此案有太多说不通的地方,想了许久仍是毫无头绪,两人久久无言,过了许久,顾勋眼神微微泛起些光亮,开口道:“也许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想用死者为我们传达某种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