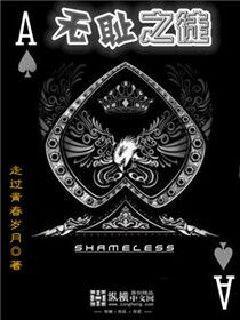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听心女版原唱 > 第31页(第1页)
第31页(第1页)
凌棠远也没睡着,我从他的呼吸声就能听出,可他不问我在想什么,我也自然不会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在所有灯都暗灭的时候问了他也听不见,就像从前一样。几次错过我说的话。唉?似乎也不对,好像他曾经听见过的样子……仔细回想一下,心中疑窦突升。似乎某次我在楼梯上轻轻说了一句,他就立即回身,那是他的本能反应,决不是动作巧合,还有,我趴在他怀里说的话,他也顺利接答了,根本没有看见我的口型,莫非……“其实……”我故意小声说。他背对着我,没回答。“凌先生?”我又加大了一点声量试探。他翻了个身,我吓了一跳,但他依然沉默,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并不气馁,又说:“其实母亲在孟先生家留下的原因很简单,她似乎认识孟先生的母亲。”没人对我介绍过那名妇人的身份,我却说她是孟屿暮的母亲,如果涉及到重要问题,他一定会反驳。可是,他还是没声音。他不会是真听不见吧?我再回忆一下初见面时的反应,掉打火机,喊他也不回答,也许我刚刚怀疑那些真的只是巧合?我慢慢蹭过去,顶着他的胳膊。最近我们睡觉添了一些习惯,我睡熟嫌热逃离他的怀抱后再想回去就必须蹭他的胳膊,即使睡的很沉的他也会条件反射性的张开胳膊给我枕,我曾为此窃喜过,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果然,他张开胳膊,我依偎上去,等他放松了胳膊我佯装无意说:“其实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说这句话的最初目的虽然是为了试探凌棠远的耳朵,但也算是真心话,慢慢沉溺在他的疼爱里,我越来越习惯身边人的存在。虽然与我曾经的设想的婚姻生活还有些距离,却也不失美满温暖,所以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先热了耳朵,觉得全身都不自在起来,有些期待他的反应。静静的房间,他的呼吸还是很平稳,我等待的回答并没有如期而至。有点小失望。既对他保留一部分听力的失望,也对他不能听到我刚刚那句话的失望。轻轻探身起来看他,幽暗光线下,凌棠远眼睛闭合,嘴唇也抿紧,像睡着了一般。我慢慢滑下去,叹口气,这人早不睡晚不睡,居然挑了这么个时候睡,真可恨。大概失望以后会激发人的困倦,折腾这么一会儿,我反而能闭上眼睛睡下去了。在丧失最后神智的时候还盘算着,从明天开始,要真的试探一下凌棠远残存的听力,毕竟好奇心已经在心底发芽,疯狂生长下根本无法压制。但愿他不会察觉我准备试探他的行为。体味幸福(上)看来凌棠远最近清闲的厉害,凌翱也不用回,整日留在这边,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从早起就支着半个胳膊盯着我看,等我睁眼时,他的脸距离我只有几厘米,眼睫毛带着晨曦朝露在和我说哈罗。这种场景有点惊悚,我倒吸口凉气不动声色的往后躲躲身子,“早。”他脸上是孩子般的坏笑:“早,昨晚睡的挺好?”我眨眨眼,想起昨晚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自然的笑笑:“是……是挺好的。”他咧嘴:“哦,那挺好。”“是挺好的。”我喃喃的低下头,突然觉得两个人对面说好几遍挺好是件再白痴不过的事,所以推推他的肩膀:“我要起床了。”“好。”他一脸灿烂笑容,出乎意料赞同我的提议,让人觉得更加的诡异,眼下所有不正常的举动只代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的脑袋被什么东西撞击了。洗漱时,他自己闷头嘿嘿直乐,看得我毛骨悚然,我一边警惕的看牙刷上有没有他捣鬼的可疑物体,一边照镜子看看自己嘴角有没有残留口水的痕迹。凌棠远还在笑,我越发越觉得事情不正常。吃饭的时候凌棠远居然破天荒的喂我吃麦片,一把银勺子盛满了燕麦粥抵在唇边,我进退两难,好不容易战战兢兢张嘴含住,抬头又发现他还在笑。我觉得这一定是他早上趁我没醒时想到的折磨我的新方法,而且就我的反应来看,此方法颇具成效。整个一上午我就在他让人想死的诡秘笑容中度过,全忘了昨晚想要试探某人听力的事。刚吃过早饭,孟屿暮来电话,范阿姨接了电话,说他准备亲自送我母亲回家,我想通过电话道声谢,还没等站起身,凌棠远阴沉着脸说:“他应该的,谢什么。”说完还瞪了我一眼,似乎嫌我多事。我觉得,他和孟屿暮之间的感情也是微妙的,一会儿是仇恨,例如对待方静时,两个人不自然的对抗,一会儿是亲密,例如在没有旁人时,他与他的默契。他对孟屿暮的感情似乎比我还多了些什么,仔细想想,有些奇怪。既然骨子里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那么相似?我叹口气挺了挺腰,准备上楼穿上衣服去花园透透气,他在背后突然沉了声音:“你干什么?”也许,他以为我生气了。我不以为意,随口回答:“不干什么,穿衣服。”“多穿点。”他哦了一声,跟着回答,与此同时,我和他同时意识到他的失误,我停了一下脚步,没有回头,继续向上迈步,心中怦怦乱跳。而凌棠远便沉默到底,死也不再开口。我知道了,他一定能听见。我发誓冬日的暖阳还是很珍贵的。家乡和背景不同,即便是冬日,空气里都是湿润的气息,吸在鼻子里凉凉的,顺到心里的惬意,北京则不然,一口气下去,觉得嗓子火辣辣的干,喘口气鼻子都跟着疼。听说东北内蒙山西更是如此,没有领教过,想想都觉得可怕。我挑了一块干净的地方靠着,看着枯枝百无聊赖的发呆。不知什么时候凌棠远走到我身后,伸过手来霸气的拉住我衣兜里面的手,用他温热的掌心给我冬日里最简单的暖,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暖。他轻声说:“想问什么?“我淡淡笑着:“不想问。”“为什么不想问?”他急急的拽过我的肩膀看着我,似乎我的无欲无求激怒了他。我很轻松的看着他,长长的睫毛,深邃铜色的眼眸,高挺鼻梁下,坚毅的嘴唇紧紧抿着,像个可爱的大男孩。没有秘密的他似乎变得更普通了,在我心里,他已经再普通不过。但内心里我还是有些高兴的,至少,他能听见,也能听见我对他呢喃过的所有言语。突然又想到昨晚自己发傻时候试探他的话,恨不能就地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不是他太会装,我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太可恨了。“你太聪明了,怎么办?我发现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看出我的窘意,他嘴角微微上扬,虽然说的是情话,听起来却像嘲讽。“我该感恩涕零?”我迎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他的眼底隐藏太多的真实情感。见我酸酸的回答,他抿嘴乐乐:“你哪次能真感恩涕零了,我才真要感恩涕零才对。”我低头回答:“别,我可承担不起。”“我失聪过,现在右耳有听力。”他若无其事的在衣兜里鼓弄着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扳过来,掰过去,像似威胁。他在用行动说,只要你说出去,手指就别想保住了。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是懊恼的反击:“反正,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了。”他青了脸:“正常女人知道自己男人听力好着呢都会高兴,你现在是什么反应?“正常反应。”我用空闲的左手揪了几段枯树枝掰弄着,他瞅了我一眼:“我看你是心里没我……”说了一半他又噤声,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这位大爷着实不好侍候,心里有他的时候,他让我别爱上他,心里没他的时候,他又抱怨心里没他,难道是让我变成既要心里有他,面子上又表现出不爱他?似乎,我就是这样的,那他还有什么不满?看来,我们俩都是别扭的人,两个性格为负的人加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得出正数来。见我只笑,他也笑了,靠在我身旁搂住肩膀,一同靠在院墙边,享受我们这个年纪该有的阳光和惬意。后来,在花园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没有说人物,没有说时间,没有说地点,听上去像个很普通的豪门故事,只是故事背后有着胆战心惊的内幕。有个男孩子和母亲过了十几年的东飘西荡的生活,母亲从小就告诉他有些东西他一辈子都得不到,一辈子。直到他亲眼看见二叔和母亲协商以他换取父亲的继承,条件是父亲永远不再出现。父亲的结局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隐形条款,他从此再听不见任何声音。母亲知道护士做了手脚后异常暴怒,但无可奈何,她不会为了这样小小的失去放弃继承和同盟,所以暗自吞咽打落的牙齿,把儿子推上继承位置,但她总觉得心中郁闷,便四处想办法找人治疗儿子的病……一次次重燃希望,一次次无功而返。实际上,只有这个孩子心里明白,他有一部分听力已经能在多次治疗后渐渐恢复,但他现在谁都不愿意相信了,包括他的母亲,所以他营造了一个失聪的环境让心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