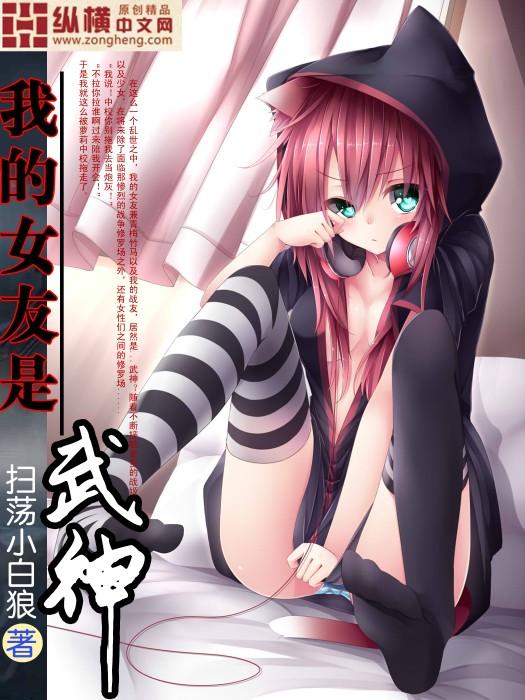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吾家有女未长成 > 第68页(第1页)
第68页(第1页)
肃安推开门,见此场景,自然恨不得自己没出现过,可是手上还端着暖炉,只得硬着头皮进去,破坏这份和谐。“你手凉得厉害,快坐下烤火。”林牧远拉着陶书容的手,让她坐到他身旁。肃安暗自叹气,他也湿了一身呢,怎么没人关心关心他?不过,只要小姐和姑爷好好的,就是他病一场也值得了。肃安回了房,一个人无聊地烤火。这边陶书容却又站起身来,帮林牧远擦头发,“头发湿着,最容易生病了,还是赶紧弄干它。”不再有水珠滴落了,陶书容又坐到林牧远旁边,将他的头发梳顺,理在手中挨近那暖炉。陶书容似是想到了什么,突然笑出声来。林牧远满心疑惑,可是看她笑也忍不住笑了,道:“你笑什么?”陶书容轻轻叹了声气,如实答道:“我在想,我笨手笨脚的,若是将你的头发烧了,可怎么办?”林牧远忙把头发握到自己手中,却叹气道:“若真如此,烧了便烧了,还能怎么办?”“你可以气急败坏地骂我一顿,或者也想法子烧了我的头发,权作报复。”陶书容道。林牧远笑道:“冤冤相报何时了。”“那你如何咽得下这口气?”陶书容问道。“我哪里有什么气非要咽下?”林牧远反问道。“我烧了你的头发呀!这样的仇应该非报不可的。”陶书容道。“原来如此。”林牧远笑道。“烧发仇人就在眼前,你还笑!”陶书容急道。林牧远还是笑,他的头发还好好的,只不过是她假设了一番,怎么这般入戏?“可你没烧我的头发呀。”林牧远无奈道。“假如我烧了呢?”陶书容又逼问。“你为何要烧我头发?”林牧远笑问。“我不小心的嘛,你也知道,我笨手笨脚的,什么都做不好。”陶书容说得像真的一样。林牧远又笑。“不许笑!快说话。”陶书容道。“说什么?”林牧远装糊涂。“假如我烧了你的头发,你会怎么报复我?”陶书容道。林牧远思索片刻,柔和笑道:“你既然不是故意的,无心之失,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我自然就原谅你了。”陶书容不满意,“那怎么行呢?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原谅了?”“那我该如何?”林牧远又问。“你可以烧我头发呀。”陶书容一脸认真道。“可我既不能打你骂你,也不能烧你的头发啊。”林牧远无奈笑道。“怎么不能?你武功这样高,你打我骂我,我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若是要烧头发呢,你也可以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下手。”陶书容道。“真要问为什么?”林牧远认真问道。陶书容点头:“当然是真的。”“因为……我舍不得。”林牧远认真道。陶书容一时无语,林牧远的话她只当是调笑,可是她说不出更有力的话去驳他,只得沉默。静静坐了一时,头发干了,林牧远又将头发束起。“啧,好一个丰神俊朗的美男子啊。”陶书容忍不住赞叹道。这话一出口,两人皆是一惊。他们之间本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云,隔着雾,隔着天煞孤星的命格,隔着一句承诺。如今,云拨开了,雾也散开了。她不是天煞孤星命。那她的承诺,可以不作数吗?作者有话要说: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陆游《观村童戏溪上》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高鼎《村居》村居这首诗是清代的,本来不想用朝代这样靠后的诗,但实在是非常应景,也暂时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所以还是用了这一句。这两首诗都写得特别好,童趣简直能溢出来。写到章节末尾,我自己还挺感动的,觉得男女主真的是很相配,想祝他们白头到老。☆、告白她的承诺,可以不作数吗?她很希望可以,但是大约不能。她的那句承诺,不仅是因为他只是她不得不应对比武招亲的权宜之计,更因为他有婚约在身。他本就不是可以由她选择的。陶书容将自己那些心思和念头一一压下,轻轻叹了声气。肃安来敲门,请他们下楼去吃饭。一开门便看见林牧远笑得开心,陶书容却是愁容满面,察觉到气氛不对,肃安只觉得自己倒霉。陶书容理了理头发,也跟着下楼。又是一顿没什么滋味的饭,陶书容默默吃饭,林牧远和肃安聊得开心,但她不感兴趣,便也没仔细听。吃完了饭,陶书容正要上楼梯,却觉得背后有道目光盯着她,让她有些心慌,她一回头,客堂中只有些普通食客,无甚特别。回了房,她始终有些担心,有人在盯着她。会不会是爹爹派的人,竟这么执着?林牧远坐在榻上看书,她凑过去,低声问道:“那位姑娘的事,你未同其他人提起过吧?”林牧远点了点头,却是不解。“那那位姑娘,如今在何处啊?”陶书容又问。“应该是在宿州。”林牧远没有丝毫犹豫。“那我们明日便动身往宿州去,只是若是与旁人说起,你便说师父可能是往宿州去了,我们去找他。”陶书容压低了声音。林牧远点了点头。要这样快就动身吗?那有些话,该对她说了吧?“书容……”林牧远唤她名字。“怎么了?”陶书容见他似乎欲言又止。林牧远正思索着该如何开口。“跟着我们的人又有什么动静了么?”陶书容问。林牧远摇了摇头。“确实有人盯着我们,我很确定。”陶书容道。林牧远一愣,大约是心事太多,他居然没有注意到。“那我们今后,在有人的地方,得亲密些。”陶书容道。林牧远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陶书容正要叫肃安起床,准备动身,进了肃安的屋子,却发现肃安脸色苍白,表情痛苦,大约是病了。“怎么了?”陶书容问道,她抬手摸了肃安的额头,并未发热。“我只是有些头疼,故而起晚了,小姐是有什么吩咐吗?”肃安忙起身。“没什么事,只是你平日都起得早,今日还未见你,我便过来瞧瞧,你好生休养,我去请个大夫。”陶书容道。肃安病成这样子,他们的行程只得延后了,这事儿还得向林牧远解释一下。陶书容心里想。她又去了医馆,请了大夫。大夫说了无大碍,她才放心。林牧远出门去了,陶书容也找不到别人,只得坐到肃安床前照看他。好在只是端茶递水,肃安大约还有些什么别的需求,也不敢明说。比如人有三急,怕也只能憋着。折腾了一上午,肃安已经有些精神了,再三保证自己没事了,才把陶书容请出了他的房间。陶书容正郁闷着,便看到林牧远回来了,就让林牧远去照看肃安。肃安年轻,身体好,到了晚上,像个没事人一样,和林牧远谈天说地,精神足得可以聊到天亮。“真的好了?”陶书容忍不住问了一句。“那是自然,我这身体,壮得像头牛,自然好得快。”肃安一边说还一边比划。陶书容看着肃安那瘦弱的身板,不禁失笑道:“那明日可以赶路吗?”“可以啊,别说赶路,就是下地干活,我也可以啊!”肃安活动了下四肢。陶书容点了点头,笑道:“那就好。”“小姐,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肃安问道。陶书容表情不大自然,垂首道:“宿州。”“宿州?去宿州做甚?”肃安又问。陶书容抬起头来,蹙眉道:“我们还未见到姑爷的师父啊,总得找到他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