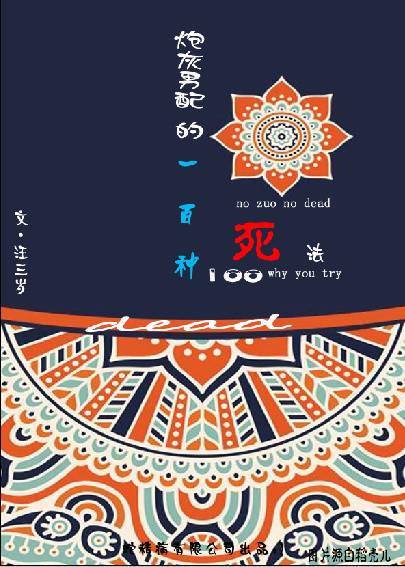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女巫pan > 第七章 女巫觉醒(第1页)
第七章 女巫觉醒(第1页)
最近宛昕总是做一个梦。梦见漆黑的晚上,她一个人走在汉京城的路上,路上爬满了蛇。这些神秘的动物环绕着她,跟随的着她又带领着她来到一片密林。赤脚踩在林中潮湿温润的泥土上,宛昕觉得身上一点点被一种新的力量充盈着。渐渐的,宛昕看到前方有点点亮光,十三个样子各异的女人围坐一圈,看到宛昕,她们露出诡异的微笑。
连续三天,都是这样的梦。第四天早上,宛昕被宛晨叫醒,“宛昕,我们先去逛街。下午去小姨家玩!泉叔叔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大秦美酒,香味浓郁,色如宝石。你这屋里太脏啦!你晚上干什么了?”宛昕连忙下床,看到地上星星点点的黑色泥土,心中一惊,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她也分辨不出了,“我让小殊来打扫,我们走吧。”或许小姨能告诉我点什么吧。宛昕想。“小姐,涂了药再出门!老爷吩咐的。”小殊道。
宛昕一脸不情愿,“这药就是唬人的。学堂里所有人都涂,屋里一股子奇怪的药味。我就不信这鬼药有用。”“宁可信其有啊,小姐!我觉得有用呢!”小殊继续坚持。“好吧好吧,快给我们涂了,我们好出门!”宛晨妥协。
那时的汉京城里容纳了太多令人着迷的事物。东市里琳琅满目的上等物件,丝绸、摆件、金玉珠宝令人目不暇接。还有来自异域的货物更是吸引人。那里有着汉京没有的一切新鲜玩意,香料,首饰都与大成国完全不同。还有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有的美若天仙,有的简直像是书里的妖怪。他们都会跳舞。不同的舞步,有快有慢,一旦跳起舞来,每一个人都变得美丽起来。
闹市中有一处算命摊子,一位算命的白面先生叫住了他们两个,“小恩客,算一卦吧?”
宛晨挑眉,“算卦做什么。”
“可知今生祸福。”那白面先生淡淡的回答。
“我不信这些。不过算一下倒也没什么。”宛晨笑嘻嘻说道。
宛昕在一旁不置可否。
宛晨说,“先生我是丙辰年生人,正月十一,巳时出生的。”
那白面先生,默默写下:丙辰,庚寅,壬辰,乙巳。思索片刻,对宛晨说:“这位小姐命带魁罡,个性耿直,聪明果断,善用权力,赏罚分明。魁罡本是制服众人之星,擅长领导。”
“那么是好的了?”
那先生继续道,“魁罡本无吉凶之说。天上吉星凶星,遇见魁罡都要退避三分。鬼魅都会惧怕魁罡星。是以魁罡星适合从军杀敌或入大理寺决人生死,不仅于自己无损,还易握重权。”
“虽是如此,凡事有利有弊。命带魁罡有什么不好之处?”
“自然是有的。命带魁罡,婚姻不顺。尤其是女命。男子尚可决定自己命运,手握重权,婚姻即便晚些亦不愁。女子若有此星,感情不顺,一辈子就难说了。”那先生说完,还将头微微一侧,看向宛晨。
宛晨面有愠色,心中不可避免地忐忑起来,口中说到,“小殊,给这位先生些银子。白费了这么些口舌。咱们也该回去了。”说完扭身便走。
宛昕和小殊只得匆忙将银子付给那白面先生。那先生只得匆匆告诉宛昕,“小姐,25岁是个坎,你们姐妹要小心。”
宛昕道声多谢,便追向宛晨。“宛晨,你生什么气。”
“我没生气,我根本不信他信口雌黄,竟然咒我。”
“不信就好。这种玩意儿听过便罢,不要当真。去小姨家喝点美酒就好啦。现在就去吧。”
住在汉京的不庸不凡,也渐渐长大。平三江看着孩子们的伤痛慢慢被抚平,内心感到安慰。最吸引不凡的的是高丽人的店铺。不凡醉心于那里的各种胭脂水粉。也不知是什么缘故,那里面卖的胭脂水粉涂出来就是自然。不凡还喜欢那儿的木槿花汁,香气怡人。买回去洒在房间,经久不褪。只是每次到这儿,春雯总显得惴惴,催促着孩子们快走。
新鲜劲过去,不凡不庸渐渐觉得百无聊赖。平三江武举出身,做过左卫长史。虽然识字,但文采什么的可以忽略不计,在官场上也没有什么大作为。一生最骄傲的便是有了莫言和莫愁。
因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常常受闲气。平三江在学习上的苛刻全用在孩子身上了。儿子莫言进士及第,做了太常卿。莫言,人如其名,话少得可怜。看见自己的外甥们,虽然满心疼爱却总不知道说些什么。莫愁蕙质兰心,聪慧可人,写文章总得到先生夸赞。但是却因爱情,抛却所有,教起孩子来也不够成功,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小孩子天生不爱学习,金娘子又不肯苛责,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成效。
平三江疼爱两个孩子。不管什么要求,孩子只要说出口,平三江都立刻吩咐人去办。动作慢一点都不答应。只有一件事,他从不放松,就是功课。不凡作为女孩子只是陪哥哥一起读书,外祖父没什么要求。对不庸,平三江的严厉完全展现出来了。
刚开始念书的半年里,不庸贪玩,好多次被外祖父训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下来。春雯也在一旁忍不住心疼。这时都是不凡撒娇,救下哥哥。半年过后,不庸被外祖父管教得玩心没有那么重了,倒还好了。
当然,两人的学问还都进益了。不凡作诗常有巧思,不庸赶不上。不庸作文擅抒壮志,不凡也比不了。两兄妹各有所长,每次先生跟平三江讲这两位学生的进步时,平三江就喜不自禁。
他就是那种喜怒都行于色的人。他的夫人江氏从他年轻时候就时时劝告他别太直,容易得罪人。他每次说了不合适的话,心里都暗暗说,“平三江啊平三江,下次可不敢这样了。脾气真该改改了。”到了下次,情绪一上来,就又不论什么,又开始得罪人。他让多少人不舒服,不肯再登他的门,他都无所谓。唯有一个人,他觉得对不起,但是事已至此,什么也改变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