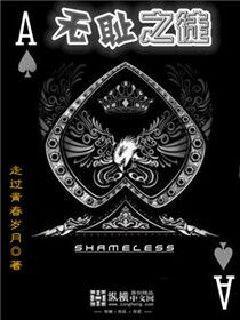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说你好你说打扰txt > 第13页(第1页)
第13页(第1页)
陆觐然坐在病床旁,看着床上那人——那撮小脏辫还真是她的晴雨表,此刻蔫蔫的,就跟她的人一样。公立医院排位已排到明年,只能通过宋栀找了相熟的私家医院院长,才落了个这么个清净的病房。或许真的因为太清净了,一时不查陆觐然耳中就飘进一把紧绷到声线都尖刻了的嗓音——“小脏辫!”萧岸冲进套房的那一刻,就是这么喊的没错吧?说到米兰……萧岸当年不就是polii毕业的么?一些原本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正慢慢拼凑着,眼看就要拼凑出些什么,病房门却在这时被人悄然推开。陆觐然面无表情地回头,只见萧岸站在门边,似乎正犹豫着要不要进来。见他回头,萧岸倒像是松了口气的样子:“她没事吧?”“体力透支加上发烧,不是什么大问题。”萧岸瞟一眼病床,眉心便蹙了起来。那眼神里包含的寓意太多,以至于陆觐然都没忍住试探:“你们认识?”“不认识。”萧岸回答得很果断,仿佛还觉得这短短三个字说服力不够,自然且肯定地补充道,“她不是您安排给我的拍档嘛,这几天工作量肯定超负荷,我只是担心她撑不住。”这么一说,陆觐然倒是笑了:“那是你没见识过她火力全开的样子。”陆觐然手机响了,他把声音按掉,起身就朝门边走,看样子是要去走廊接听。萧岸侧了侧身让他出去。这通电话是宋栀打来的,显然她也很好奇,他才来米兰几天,怎么就结识了那么多她之前闻所未闻的朋友。“你那朋友还好么?”“就那样吧。”他语气倒是满不在意,眼神却不自觉的往回一瞥,只见之前一直踟蹰不进的萧岸此刻一闪身就进了病房。“听院长说是个女生。”“那院长还挺八卦。”“人一男院长,对漂亮女生当然稍加关注。”“漂亮?”那是那院长没见过她龇牙咧嘴啃龙虾的样子,陆觐然失笑,“那院长眼光倒是挺特别。”“宋姐约你的午饭你也赶不上了吧?”陆觐然抬腕看一眼手表,已经12点多了,“下次。下次一定补上。”“宋姐早就料到啦,”电话那头传来一丝笑意,难辨真假,“哦对了婚礼当天宋姐让你把你那朋友也带上。宋姐对你那朋友特好奇,就想看看是谁那么大能耐,能让你为了她连续爽约这么多次。”陆觐然刚要开口,余光就瞥见有一抹身影刚从病房里出来。扭头一瞧,果然是萧岸。萧岸指了指自己腕上的手表,看样子是赶时间要走——婚礼近在眼前,确实片刻都不容浪费。“宋姐那是瞎操心,就一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朋友。”陆觐然一边回着电话那头的宋栀,一边摸出备用房卡递给萧岸,做一个打电话的手势——有什么问题立刻联系我。这原本是为小脏辫备着的房卡,无奈小脏辫在他这儿信用度太差,他担心她一言不合又开溜,就迟迟收着没给。只不过她现在就算想溜,也有心无力了……陆觐然这么想着,不由瞟了眼那空落落的病房门。钟有时吓傻了——本来刚醒那会儿,迷迷糊糊地眼皮特别沉,就只能闭着眼睛吸吸鼻子。可惜鼻子堵了,嗅觉视觉全部失灵的情况下,只能靠身下的柔软度判断,她现在应该是在床上而不是在地上。看来是哪位好心的服务生路过看见她晕倒,这才搀她到床上休息。可钟有时刚松一口气,心尖又蓦地一紧——她当时穿的可是长裙,摔倒的时候姿势优不优美?会不会露底?她穿得可是条大妈底裤,万一真露底了……画面太美不敢想。当然不容她继续乱想的,还有那随即响起的脚步声。房间里竟然还有别人?而且那脚步声分明离她很近,她都还没来得及睁眼,就有一阵微风拂动了她的睫毛——那脚步声的主人分明朝她俯下了身。继而,吻了吻她唇角。那人一手抚在她脸侧,指尖的力道轻若无误,似乎怕弄醒她,手表的表带却只印给她一片凉意……萧岸走后没多久,陆觐然也结束通话回到了病房。也不知这小脏辫到底要昏睡到几时,正这么想着,眼前就无声地滑下一溜鼻涕——睡着了都能流鼻涕?陆觐然不得不服,抽张纸巾,俯身准备帮她擦鼻涕。手还没碰着她就停了——这女的突然间浑身僵硬,特别明显。陆觐然一挑眉:“醒了?”她睫毛一颤,分明听见了他的话,却迟迟没有半点动静。陆觐然就抱着双臂站床边,看她终于慢条斯理地睁开眼睛。她面无表情地对上他的眼睛,陆觐然刚要开口,却发现她的视线又慢慢下移,径直看向了他的手表。那只是手表,又不是洪水猛兽,何至于她眼底一点一点泛上惊恐?陆觐然都被她看得心里发了毛,下意识的将戴表的那只手背到身后,另一手稍不客气地拍拍她的脸:“你干嘛?摔傻了?”她立马捂住嘴用力摇头。摇头就摇头,干嘛非得捂着嘴?陆觐然微微一眯眼,眼底满是不解。这女的肯定是摔傻了。开了点药她就能出院了,他好心搀她下床,手还没碰着她,就被她挥手挡开。陆觐然看着她匆忙趿上鞋、几乎是连蹦带跳地一路飞到病房门外,眉心微微一蹙。到了停车场,他真是破天荒地好心为她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除了宋栀,谁还在他这儿获得过此等待遇?她却只是瞅了一眼那敞开的车门,二话不说立马调头拉开后座车门,钻进后座。徒留陆觐然站在敞开的副驾门边,孤单寂寞冷,郁闷纠结恨。陆觐然沉默地开着车,已经不知是第几次透过后视镜偷瞄后座。可后座那人,一直闭着眼假寐,表情都不带变。回到酒店已是下午,陆觐然那眉头就再也没解开过。她哪像是刚晕倒过的人?走得那叫一个风驰电掣,陆觐然手揣裤兜跟在两步远后,走廊上铺着如此厚实吸音的地毯,却依旧能清晰听到她那越来越快的脚步,陆觐然倒也不急,就等着看她到底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果然,不出一会儿她便停下了脚步——她没有房卡,怎么进屋?只能在套房门外不甘不愿地等他。待他也走到门边,她直接伸手,也不吭声,就这么不客气地向他讨要房卡。陆觐然慢条斯理地掏出房卡,却不给她,只是问:“几个意思?你到底是吃错药了还是摔坏脑袋了?”“……”我在冒着生命危险跟一个潜在淫魔一起工作,还要我给好脸色?可要她放弃一个能秒杀掉萧岸的机会?她又不甘心……钟有时只能以冷脸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伸手去夺他的房卡。可惜没他快,陆觐然拿房卡的那手背向身后,另一手抵墙,就这么将她牢牢困住。钟有时当即吓得花容失色。妈呀都对老子壁咚了,还说不是对老子有想法?果然,淫魔已经忍不住要挑明了警告:“你再这样不肯配合,就直接给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配合?怎么配合?一想到那肮脏的画面,钟有时就气得直哆嗦。看她那不明所以的眼神,不知所谓的反应,陆觐然心里默默叹口气——这女的,多半是真傻了。也不知怎的就心软了,换做平常恐怕真的要叫她收拾东西滚蛋,如今却是叹口气,再叹口气,最终只是抬起手摸摸她的额头:“是不是烧没退,烧傻了?”他的手挨着她的脸,手表的表带印给她一片凉意。皮肤的记忆甚至甚过头脑,只是这一星半点的凉意,便顷刻间将钟有时拉回到一个多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