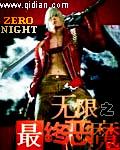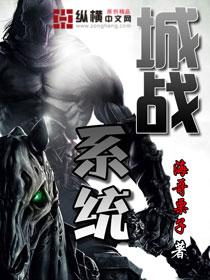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智能工厂与灯塔工厂的区别 > 第一千二百二十五章 古文课程(第2页)
第一千二百二十五章 古文课程(第2页)
之前主要是背诵,现阶段还只是四书的基本内容,五经暂时只要求能够通读,就是说必须识文断字。
按照李兆伦的说法,学习古文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学习古代汉字。
在这个时代,也有人提出了使用拼音代替汉字的说法。当然那个家伙现在在学术界臭名昭著。已经无法继续留在国内,混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
也有人提出精简文字,也就是在官方教育中,使用简体字来代替古汉字。
但还是遭到了学术界的驳斥,这里面除了文化传承的问题,还涉及到汉字本身的意义和神韵。
就以“龙”和“龍”这两个代表着同一个意思却有着不同的书写范本的字为例,简体字明显和龙没有关系了,完全是为了简化而简化。
“龍”字所代表的意义,使人一见便知晓其意,那是因为有着神韵在其中。
至于说简体字能够更好的促进商业发展。那更是胡说八道,即使是原本的时空里,使用简体字的地区经济不见得比使用繁体字的地区要好吧。
无论是商业还是生活,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只是为了方便,不如都去学习英文好啦,反正就二十六个字母。
不过现在,连飞逸也没心思去理会这些,他还只是个小人物,关注的也只是他个人的学业问题。
还是导师李兆伦的那句话:若想学好文言文,必先学好古文字。
所谓的“古文字”,这个名称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
而李兆伦在他的课堂上所提到的古文字,主要指见于考古资料上的早于小篆的文字。
他还在他的《谈自学古文字》一文中,多次提到“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如果想学好古文字。必须掌握古文字学之外的很多知识。
按照连飞逸他自己的体会,在必须掌握的那些知识里,最重要的是古汉语方面的知识。
古文字是记录古汉语的,如果对古汉语很不熟悉,就没有可能学好古文字。而如果想要熟悉古汉语,那么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多多阅读古书。
连飞逸很轻,他现在的条件,已经跟古时代的读书人完全不一样了。
古代一书难求,所以很多人甚至可以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八一本书读通读透,甚至理解出更多的东西来。
可连飞逸却不可能像那些人一样。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去读某一本或者几本书,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作为知识的载体,写满文字的书籍也大量流传,开阔着新时代读书人的眼界。
大量阅读和系统性的选择。才更加适合如今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连飞逸不用像以前的学子那样死守着四书五经不放。但也不能随意看过就算,至少要想法集中时问精读一部篇幅适中的比较重要的古书。
按照他导师李兆伦的说法,对学古文字的人来说,最适合精读的古书也许可以说是《左传》。《左传》的注本有好几种,李兆伦就主张他的学生们去读《十三经注疏》里的《春秋左传注疏》。
不仅是《左传》的本文,就是注和疏基本上也要一个个字地读。
这不但是为了帮助读懂本文,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古代注疏的体例。读完了这部注疏,以后使用其他各种注疏就比较方便了。
读《左传注疏》时可以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当作参考书。读《左传》不但能熟悉先秦语言,而且还能得到很多先秦历史、社会、典制、风俗、思想等方面的有血有肉的知识。
这些知识对于学习、研究古文字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除了《左传》之外的古书,当然也是要多去阅读的,但是由于时间和个人精力等条件上的限制,读法恐怕就只能以“独观大略”为主了。
李兆伦就经常在他讲课的时候提到:“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
连飞逸当时也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本人就对战国文字很感兴趣,所以特意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借阅了《战国策》、《史记》和诸子等书。
不过现在所能看到的战国文字资料,多数是语言带有仿古意味的金石铭刻。以及文字特别简单的玺印和古代货币。
因此对学习、研究战国文字的人来说。《战国策》、《史记》等书的史料价值超过作为语言资料的价值。
与读古书同时,最好看一点讲上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的著作,使自己的古汉语知识有条理。初学者可以看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的通论和王力《汉语史稿》中、下二册里的有关部分。
熟悉古汉语,主要靠踏踏实实读古书。
如果古书读得不够踏实,古汉语方面的通论性著作读得再多也不解决问题。初学者如果读了不好的通论性著作,反而会使思想混乱,甚至还会误入歧途。
在这一点上,连飞逸也是在进入了宏立书院之后才知道的,与公办学校那种完全就是背诵、默写和白话文翻译的套路不一样。
难怪,大学更喜欢从私立学校招收学生。哪怕文化知识课程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达到良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