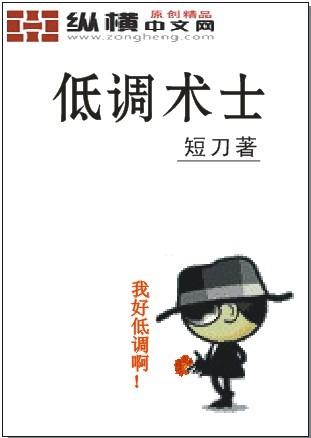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新生凹凸世界 > 番外一 你我的奋斗3(第2页)
番外一 你我的奋斗3(第2页)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盛比拉堡的冷风就已经把杰维拉·真托继斯叫醒。
他睁开眼看向窗外,带着朝雾的早晨,远处的田边,淡橘色的太阳似是要升起。
他知道,他要回家了。
到站后,他先是去到了自己的叔叔家,在那里他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真托继斯,你大学读完了吗?”
叔母问他。
手里面是刚做好的吃食,一份浆糊汤,看起来像是土豆与萝卜打碎,加了一些晒干的豆类。
“嗯,差不多了,回来参加母亲的葬礼,过段时间我再回去。”
真托继斯对于自己的家人算的上友善。
“啊?你父亲没跟你说吗?你母亲不办葬礼的。”
叔母放下手上的浆糊汤,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说。
“没关系的,你很努力,也很有本事,你的母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叔母见他没有反应,接着说。
“要不你再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别介意,再过几天就是春种了,家里正好缺个人,你表妹你也知道,去年被人骗了,现在还在一个什么革命党里面工作,见不到面。”
“唉。”
女人唉声叹气着,她实在想不到自己那向来乖巧的女儿,为什么会跑到那些地方,连家都不要了。
“婶婶,把这信寄给我的父亲吧,我过段时间就要离开了,田里的事情我估计忙不过来了,今天下午我就走了。”
真托继斯说着,打发走了自己的叔母。
他靠在椅子上,这里是他表妹的房间,虽然从去年开他的表妹就没再回来过,可整个房间依旧是一尘不染,看的出来他的叔母很爱她的女儿。
等到他喝完那碗浆糊汤,在碗底压了20卢卡森,他就选择了离开。
他知道今年的春天注定不会安宁。
他走在大街上,身上是他带回来的行李。街道上总有人会时不时的看向他,那张维拉其人的脸,总会给英格拉姆的人带来别样的既视感。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群人看向他的目光总是带着些许担忧。
直到他走在去驿站的巷口,突然冒出来几个身穿英格拉姆警服的中年男人,将他按在身下。
他第一时间是打算反抗,可在看到对方的警服后他又下意识的卸了力,任由对方将他制伏。
他的身形相当健壮,只要他乐意在这无人的小巷里,他可以把这三个人全部撂倒在地。
作为维拉其人这是他的自信。
“警长,我犯了什么错?”
被押入警局的真托继斯问眼前的就几位警官。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再看向他,他们相视一笑。
一个看起来比较臃肿的警官走上前来,他的笑容看起来十分的和善,只是那被赘肉遮住的小眼睛,让他变的极其猥琐下流。
“小朋友啊,没什么的。”
“只是问你几个问题罢了。”
“回答的好,我们就放你走,回答的不好,哈哈!”
男人笑了笑,引的身后的几个男人也笑了起来。
真托继斯皱起了眉头,他知道情况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
他的手被椅子上的锁链卡住,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
他阴冷的目光内敛开来,沉默着等待对方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