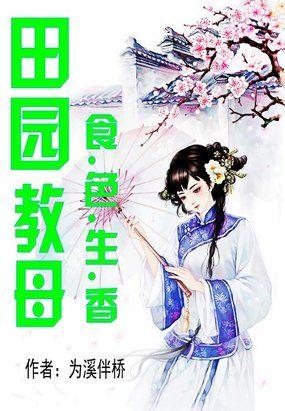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此话当真后一句最佳答案 > 第21页(第1页)
第21页(第1页)
喻嘉惟本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却在人生的挫败中终于心灰意冷,他什么都不想要了,唯一的愿望是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画展。
喻嘉惟把房子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不值钱的家具衣物,或是买了废品,或是捐了,他想圆自己一个梦,他用所有的钱,求美术馆的老板让他开一周画展,此后他就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这个世间。
其实喻嘉惟不想死的,他多么希望自己能从黑暗中拔出来,再次面对生活。
之前支撑着高昂的医疗费都熬过来了,只要自己愿意,卖画,投稿,生活总能回归正轨。
可是喻嘉惟不停地画,不停地画,回过神来,却只有绝望与黑暗,他已经被黑夜彻底吞没了。
他觉得自己就像颗暗淡的小星块,在无尽的夜空中,他的光芒微乎其微,照亮不了任何人,包括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景盛出现了。
景盛跟段亭打了个电话,简单说明了自己有要紧事,让他不用等自己了。
将手机放下,景盛回头看见喻嘉惟在小心翼翼地整理着他的画,美术馆的主人在旁边睨着他:“这可是你自己提前要收的,剩下一天半的钱我可不会退你。”
“没关系的!谢谢您。”
景盛看着他封上一个箱子,走到他旁边:“这可有点头疼呀,这么多,我在这也没车,有点难搬,还得去你家收行李呢。”
谁料喻嘉惟轻轻摇了摇头:“我,没有行李。”
喻嘉惟不敢说,自己全身上下现在属于自己的东西,除了这四十幅画,就只剩下背包里那瓶安眠药了。
看出了喻嘉惟的情绪变化,景盛体贴地什么都没问,只摸了摸他的头顶:“也行,反正回去了,什么都可以重新买。”
回程,景盛为了那几箱子油画,花了极大一笔运费,支付的时候,喻嘉惟急得眼眶都要红了,说要丢掉。
他自己就已经花了两千多的机票,现在这些画又要花掉景盛这么多钱。
喻嘉惟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钱,早两年是要精打细算给父亲买药、做化疗,后来父亲病情恶化住了院,他每拿到一笔稿费,总是急匆匆地打进父亲的医院账户里,就像一个无底洞,有时候喻嘉惟晚一两天拿到钱,就得饿一两天肚子。
景盛救下了自己,他夸自己的画好,他说要雇自己,可是自己还不一定能帮他赚钱,他就要倒贴这么多,喻嘉惟心里不安,要去抢快递单退款。
景盛把单子换了只手高高举过头顶,喻嘉惟够不着,急得带上了哭腔:“景……景先生……”景盛大手按着他的头顶:“别哭,嘘,没事,这些钱算什么,等你以后出名了,我把它们卖了,就都赚回来了不是?不许哭。”
见喻嘉惟艰难地憋住了,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景盛又忍不住要笑。
喻嘉惟没有外套,现在套着的是自己的羽绒服大衣,更显小了一点,景盛总有一种自己在欺负小孩的错觉。
他把小朋友往自己怀里一按:“好了好了,不逗你,允许你哭一会,好不好?”喻嘉惟脖子一僵,果然没绷住哭出了声,已经好久没有人对他这么好了,喻嘉惟又欣喜又害怕,劫后余生的他在景盛怀里这一刻,才真正体会到脚踏实地的安心,像是要把这阵子的孤单与委屈全部发泄出来,喻嘉惟放声大哭。
景盛轻拍他的后背给他顺着气,抬头就见段亭一脸复杂地看着自己。
景盛朝他比了个嘘声动作,就低头继续哄小孩了。
“你居然有26了?”握着喻嘉惟的机票,景盛才有机会看看他的年纪,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小不点居然只比自己小两岁。
景盛捏着喻嘉惟的下巴左右转了转:“太瘦了小惟,以后多吃点。”
被景盛捏着的脸勉强挤出了一点肉,喻嘉惟费力地应了一声,也不挣扎,乖巧地任景盛摆弄,大眼睛眨巴着看着景盛。
喻嘉惟刚刚大哭一场,眼底还透着无法忽视的红,看向景盛的眼神却满是依赖,景盛忽然觉得自己被这小朋友的可爱击弯了腰。
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第一次坐飞机,喻嘉惟像极了刚破壳的小鸡崽子,死死粘着景盛不放,景盛为了能陪他一起,偷偷退了机票重买,不敢让他知道被收取的手续费数额,怕又惹哭小朋友。
见喻嘉惟板直了身子僵在座椅上,景盛伸手在他肩上按了按,又探到了喻嘉惟腰侧挠了挠。
喻嘉惟怕痒,躲了一下,这才放松了下来,被景盛按倒在座椅上:“乖,别怕,放轻松,我在旁边呢,怕就拉着我。”
于是喻嘉惟真就在绑好安全带后轻轻拽着景盛的外衣一角,待升上了天空后,才兴奋地扒着小窗户看外面,景盛就揽着他的肩膀陪他看风景,小小声地跟他讲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