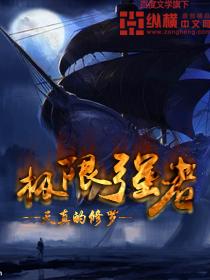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知乎 隔壁宿舍 > 第15章(第2页)
第15章(第2页)
“您一个人在这儿住吗?”
老太太进屋想给他们倒茶,可找半天也没找到干净杯子,闻言连忙点头,“是恁。老头儿没了,儿子不管俺恁。”
陈木栖素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这时柔声细语,身旁几人都不习惯了。
“那怎么还住在六楼,上楼下楼的,多不方便呀?”
老太太惴惴地望他们一眼,结巴着说,
“俺……俺不在楼下住……楼下有保安,赶人恁……”
她焦灼地看一看陈木栖,左眼似乎害了病,眯得红肿睁不开。她央求道,
“小大姐,恁还能别跟人说俺给这儿……俺都是想找个暖和地方过年,过完年都……都搬走……别跟保安说恁……管不管?”
老太太说着,腰还是一弯一弯,瞧着老天拔地,摇摇欲坠。
陈木栖心头酸楚,不落在嘴上,她抿着嘴唇点点头。
问起那件吓死人的红裙子,原来却是老太太捡回来的红袄,留着过年穿,蹭蹭喜气。
江言还记着楼梯上的小狗玩偶,问那是怎么回事,老太太就笑,笑得一张脸揉得更皱。
“那是俺家看门狗,以前给这学校的小大姐忘带走嘚,俺看怪好的,都拿回来了恁。都是……都是胳膊害了,找不着了。”
很久没人跟她说话,更是太久没有这样的小辈跟她唠嗑了,老太太见他们没有恶意,就多絮叨两句。
她扒拉扒拉自己棉袄上的破洞,说,
“这个袄俺穿怪久了,都是热的时候给那棉瓤掏出来,都能当单衣穿恁,冷的时候再给恁弄回去。等到时候俺都掏点棉儿,给那小哈巴狗的腿给缝上。”
几人听罢,都不说话了。
都是城里来的孩子,娇生惯养,平日里呼朋唤友,唱k聚餐剧本杀,即使无数次和这些人擦肩而过,也难以在意。直到现如今面对面了,才忽然意识到自己衣食无忧得多简单,幸福得要愧怍。
又陪着老太太聊了好一会儿天,临走几人把全身上下的现金都搜罗出来了,凑了不到两百的零钱塞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不肯要,一味推拒,他们只好假意收手,等下了五楼,再让游卓然把钱送上去,在老太太拒绝前就一溜烟跑下来。
他们的酒店就订在附近,只与那学校隔了两条街,可却一扫荒芜,有大商场也有街,小商小贩络绎不绝,赫然是副繁华夜景。
几人随便找了家烧烤吃,吃完便四散逛去了。
到了晚上九点半,其他三人陆续回了酒店,却没见江言与游卓然。成飞问社长,社长也是一头雾水,还是隔壁房间的陈木栖回话,说他们拎着个袋子,不知道打车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