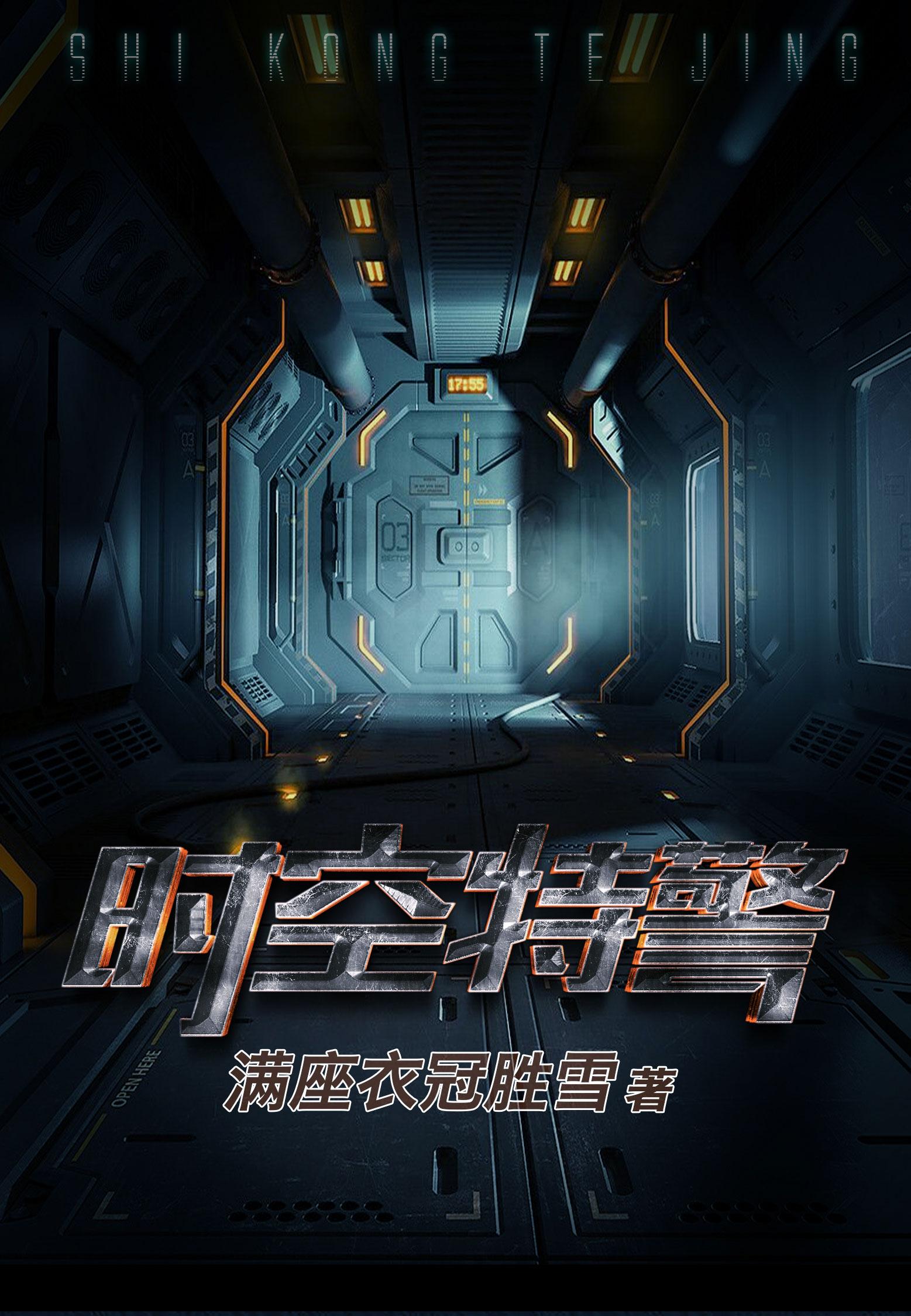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深夜文采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但照片里的这个男人不是奥尔迪斯。两人完全不沾边。
&ldo;搞什么名堂?&rdo;亚历克丝说道。语气激动得差点呛住。
&ldo;这就是他,亚历克丝。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你看看日期。&rdo;
她看了。在她右手下方有一个日期戳印:1994年1月11日。
这个人是查尔斯&iddot;卢瑟福。拍摄日期仅仅就在四天前。
[1]汉弗莱斯(huphries)根据发音分成两部分就是hupfries,即驼背炸薯条。
亚历克丝
现在
21
刘易斯&iddot;普莱恩的萨博车引擎开始呜鸣时,他已经迟了。他正在赶往迈克尔&iddot;坦纳追悼会的路上。他强开了几英里,不去理会那异响,只想着那冷血的杀人犯。想着死亡如何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刻下一条线。扯断生死的接缝,搅乱一切,让它们令人痛心地纠结在一起。经过伯灵顿边界时,泪水已在他脸颊上变冷,他摇下车窗,任凭风吹着他所剩无几的头发。
很快车身开始震动,一缕灰烟从挡风玻璃前面冒出来。他把车驶向一条佛蒙特的乡间道路,试着用手机给亚历克丝&iddot;希普利打电话。但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手机根本没有信号,不管怎样,现在再要回头已经晚了: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吊唁的人们已经在贾斯珀的四方院里聚集。(刘易斯从他与残暴、变态的人打交道的经验中知道凶手很可能就在那群人之中。)
或许这样更好,他想。作为一个心理承受力差的人,一名失败的心理医生,以及暴力犯罪精神病医院的管理员,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花了半小时拦下一辆过路车,又花了四十五分钟才进了一座叫做奥韦尔的小镇,找到一名机修师修理了引擎,师傅警告他:这车维持不了太久。很快他又回到了2号公路上。当他开进贾斯珀,看见远处校园建筑上闪闪发光的尖顶时,刘易斯猜想着这一切‐‐他的迟到、车的故障‐‐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其他人的怀疑。他们总是那样的,用犀利的、冷冰冰的眼光看待他。散热器裂了?他们会嘲弄地说,这听上去怎么这么像刘易斯的风格。
那是很疯狂,听上去就像他的某个囚犯会说的那样神经错乱,但他开始对着后视镜编了个故事,一个关于他为什么会迟到的谎言。像某种精心编排的不在场证据。
他停好车,跑向山坡上菲斯克的大房子。假如他能在其他人参加完追悼会离开前赶到,那么他还可能使他们相信他是真心在乎的。相信他一直都很尊重迈克尔,并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一场多么惨无人道的悲剧。当他跑到前门时,他的衬衫已被汗水浸湿贴在胸口,喘息声急促而沉重。
他敲了门,无人应答。刘易斯还清楚地记得他念本科时这栋房子的样子:菲斯克会经常邀请他们这九名被选中上奥尔迪斯夜课班的英语专业学生来做客。那种与其他人一起在这栋房子里的场合总会给刘易斯带来一种可悲的快乐。那就好似,只有在那些品着天价般昂贵的红酒、谈论着伟大的文学著作的夜晚,他才真正是属于这个群体的。直到他收到那部手稿前,那样的时刻都是稀松罕见的。
那部手稿。
他开始回想起来。想起它怎么到了他手里,那一页脆弱的纸,以及还会有更多的承诺。想起那匿名的保证确信未出版的法洛斯手稿就在这儿,就在这栋耸立在他眼前的大房子里。刘易斯想找亚历克丝谈谈,看她是否找到了剩余的手稿。假如他能以某种方式令法洛斯再度复活,他想着,让法洛斯起死回生,那么也许其他人就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平等地尊重他。
他转到房子的另一侧向里面打探。窗户上积满了厚厚的污垢,很难看得清里面的情况。但他确实看见了:一个人影从窗玻璃后走过。
&ldo;嘿!&rdo;他一边大喊一边猛敲着窗扉,&ldo;我是刘易斯!我在这儿!我赶过来了!&rdo;
他飞快地走到房子背后,又往里张望。分分秒秒朝他压下来,一点点地流逝,令他开始飞跑,一步跃上鹅卵石铺地的门廊,来到后门跟前,发现门‐‐
开着。大敞着,邀请他进去。他今天的第一个突破。
他走进门厅。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进来,参差不齐地照在硬木地板上。他闻了闻:那是发霉、腐朽、废弃的味道,是时间的流逝,他日渐增长的年岁,丹尼尔的自杀,还是迈克尔不合情理的被害。奇怪的是,他想起了他的一名病人,那人亲手勒死了她三岁的女儿,然后又放火烧了她的尸体。那病人对他说:&ldo;你想的也都是邪念,普莱恩博士。这就是你和我相似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相同之处。&rdo;刘易斯闭紧了眼睛,朝房间深处走去。
他的脚步声回荡着。大屋里有一盏灯还亮着,发着光‐‐但此外还有点别的什么。他们不久前还在这儿。沙发上卷着一条毯子,壁炉里堆着黑色的炭灰。
&ldo;我到了。&rdo;刘易斯朝着房间里说道,声音对着刚才他从外面看见人影的方向,引起一声空洞的回响。接着是他的不在场证据:&ldo;我的一个病人。当时医院里出了点麻烦。但我终于还是到这儿了。那边有人吗?&rdo;
他转身要走,但又听见了一阵很轻的脚步声,地板的吱呀声。他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