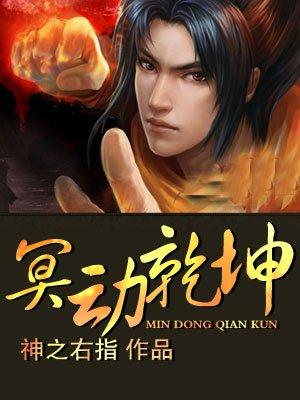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将门娇将军大人有点糙春秀结局是 > 第139章 送人(第1页)
第139章 送人(第1页)
“夫人身边也只有五个人伺候,一个奴婢却要两个人伺候,真是见了鬼了。”
影竹自进了宁康苑便止不住的抱怨。
白荷灌了汤婆子塞进被子里给宋挽煨脚,压着情绪说:“姑娘,快睡会儿吧,奴婢在这儿守着你,一会儿若是水冷了,奴婢再给你换热的。”
宋挽只是怕冷,这会儿倒是不困,缩在被子里问白荷:“眼下是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你还有机会可以选择,若是去主院,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
“姑娘,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
白荷气得眼眶有点红,有些哀怨的瞪着宋挽,好像宋挽是始乱终弃的负心汉。
宋挽笑笑,轻声说:“我这也是为了你好,是我自己要回瀚京的,如今这一切都应该由我承担,我没什么能力,你跟着我免不了会吃苦受罪,委实没有这个必要。”
若不是白荷这段时间都真心相待,宋挽也不会对她说出这番话。
白荷的眼睛更红了,说:“奴婢是在饥荒年被卖进宫里的,早就不记得亲人长什么样子,奴婢没读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却也知道情义二字最为难得,奴婢一开始的确想仰仗姑娘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但跟了姑娘这些时日,奴婢已是真心想跟着姑娘,当初奴婢没能护住公主,这次,奴婢不想再留下遗憾。”
一字一句,白荷都说得很坚决,宋挽愣了一下,而后恍惚道:“你和春秀好像啊。”
白荷问:“春秀是谁?”
宋挽脑海里闪过过去的画面,说:“她曾是我的贴身婢子,宋家被抄前,她原本是有机会离开的,但她说什么都不肯,死都要和我死在一块儿。”
白荷没再追问细节,只坚定的说:“姑娘值得。”
值得什么啊?
怎么一个个的都这么傻?
她都替她父兄不值了,她们还有什么好值得的?
宋挽缓缓摇头,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让白荷将影竹叫进来。
影竹以为宋挽要吩咐她做事,一脸的不高兴,皱着眉头问:“什么事?”
屋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叫人搜走了,宋挽身无长物,没有能给影竹的甜头,直白的问:“你在廷尉府想求什么?”
影竹夸张的笑出声,难以置信的看着宋挽,直白的问:“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你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想给我画大饼?”
宋挽说:“你是见识过我的厉害的,我绝不会任人欺负,你若是聪明,就安安分分做你的事,兴许还能有意外之喜,若非要找茬,就只剩飞来横祸了。”
许莺莺立了廷尉府的规矩,宋挽也要立一立宁康苑的规矩。
出了宁康苑,一切都听许莺莺的,宋挽没意见,但在宁康苑里,她绝不允许影竹做什么腌臜事。
宋挽的语气有些柔弱,但莫名有一股叫人不敢轻视的威严。
影竹想到手臂上的疤痕,不服气的问:“怎么,你又想划我一刀?”
宋挽垂眸,没有看影竹的眼睛,只说:“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如今孑然一身,又毁了名声,你猜我若是被惹急了,到底敢不敢杀人?”
影竹想起宋挽上次伤人时的表情,心里有点没底,一时不敢接话,院外传来小厮的声音:“宋姑娘,卫小姐来探望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