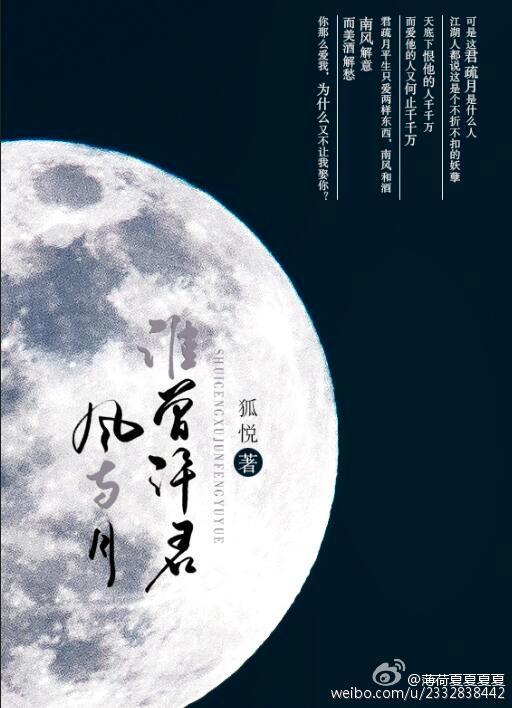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世情如纸打一动物 > 第111章(第1页)
第111章(第1页)
这一日的阳光温暖明亮,落在宣宁毫无血色的脸上,将他的脸色映得几乎成了透明。他许久没有走出屋子,在阳光中阖上眼,眉头舒展开来,苍白的嘴角扬了扬,阳光中细小尘埃漫舞盘旋着,一切静谧而美好。“阿宁,你喜欢这里吗?”苏小冬拉拉宣宁的手。桑树周边的一小块地已经被她整理得有模有样。宣宁睁开眼看了看,身边草木茂盛鲜花开得热闹,可他的注意力却并不在满地的花草间,只握苏小冬的手,含笑道:“喜欢。你在哪里,我便喜欢哪里。”苏小冬侧过身去搂住他的肩膀,埋在他怀里吃吃傻笑。两人相拥着坐了一会,宣宁从怀中摸出一只竹哨递给苏小冬,指着桑树道:“帮我把它埋在那里。”那只碧色竹哨苏小冬看着十分眼熟,回想了好一会才想起那似乎是南溪临死时塞给宣宁的。在她困惑的目光中,宣宁只好详细说:“你一会儿会挖出一个木匣子,帮我把它放进那个匣子里,再埋好。”苏小冬一抖:“那个木匣子,装的什么?”宣宁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她以为匣子里装的东西,苦笑着解释:“只是些在李家村的旧物。我后来回过一趟李家村,全村人横死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山里多财狼野狗,我,我找回去的时候,只剩下一点破碎的白骨。”说到这里,宣宁脸色煞白,按着心口猛然咳了几声,哑着嗓子继续说下去:“我无法分辨骸骨,只能将所有碎骨葬在一处,又因为无法时常回去悼念,便从每一家取了一样小物件装在这个木匣子里,埋在树下,时时追忆……”宣宁强撑着一口气说完这些,便又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苏小冬听得心惊,觉得他像是要把整颗心都生生咳出来一般,给他抚背顺气,好一会儿才稍稍压住咳喘。剧烈的咳喘耗光了他的力气,他虚弱地靠在躺椅里,半睁着眼睛看着苏小冬小心翼翼地挖出桑树下的木匣子,将那只竹哨放进去,轻轻松了口气。苏小冬重新坐回宣宁身边,握住他的手。宣宁微微阖着眼,知道她来了,并不睁眼,自顾自说着往事:“我们刚刚遇见的时候,我不肯喝粥,你还冲我发过脾气,你还记得吗?”“记得。”“我不是故意要给你添麻烦,是因为李家村被屠那日,恰好是腊月初八,家家户户都在煮腊八粥,可最后他们的血都和锅里的粥混到了一起……”苏小冬心里疼得喘不过气来,握紧了他的手:“好了,阿宁,都过去了,别想了,也别伤心了。”宣宁睁开眼,看向苏小冬,目光如水,明面上风平浪静,暗里却蛰伏着波涛暗流:“既然已经伤心了,不如便伤透吧。小冬,你跟我说说,阿秋是怎么死的。”苏小冬老老实实地从自己回京都路上遇到追杀,阿秋现身救她说起,后来是如何遇见颜韧之,阿秋是如何受的伤中的毒,一五一十地同宣宁说清楚。眼看着宣宁脸色越加阴沉,她又是担心又是害怕,搂住他的胳膊半是撒娇半是劝解:“阿秋到了最后全心全意都是要让你活下去,你好好活着,她才能瞑目。”宣宁轻轻叹了口气,摇头:“我们这样的人,生死无定,我不会因此太过感伤。只是小冬,你不该把她留在山下,她为了我万死不辞,不该死后连个葬身之处都没有。”“对不起。”苏小冬轻声道。她也一直没放下阿秋,宣宁的情况稍稍稳定后,就托岑溪派人悄悄进阵里去寻过阿秋的尸身,但苦苦找了三四轮尽皆一无所获,那时她才终于相信,进山大阵千变万化,阵法开启便绝无两条相同的路的说法。宣宁眼神幽冷:“他们是冲着我来的。”纵使伤病中孱弱不堪,他的怒意骤然而起,随之隐约生出的杀气,还是让苏小冬心里发寒。古人说冤冤相报何时了,道理她懂,可这一回她没有劝宣宁——她的命是用阿秋的命换的,她没有立场要求宣宁宽宥。“你说追杀你的陌生人使的是飞刀,你可记得那飞刀的模样?”苏小冬点头,蹬蹬蹬跑回屋里,取了一样银白色的物件递给宣宁:“就是它。”那物件约有两三寸长,通体银白,刀身上用篆体刻了个“水”字,正是青州往京都的路上,从马车外投掷进来,差点把苏小冬钉在车厢里的那把飞刀。留着那把飞刀,苏小冬本意也不是要递到宣宁眼前来告状给他添堵的。她那时虽猜测杀她的人是为宣宁而来,但那到底只是个猜测,若真是有别的什么人因为别的什么事,不远万里到青州要来杀她,可就不是江湖仇怨这样简单的事了。因而她特意留着这把飞刀,本是打算等此间事了,回到京都去,让母亲或者伯父派人好好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