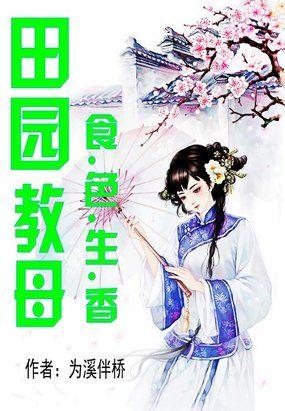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免费阅读全文 > 第101页(第1页)
第101页(第1页)
清殊听罢却摇了摇头,“带着我是累赘,只要世子殿下能找到得力的人手便是。我家家丁既然都寻到了国公府,便是走投无路了,我虽在园子里,不清楚外头的关节,可也知道堂堂天子脚下发生这样的事却寻不到救援是何等蹊跷。”“正是因为太过蹊跷,我不能再去浪费时间找衙门和护城司。”清殊仰着头看向晏徽云,清澈的瞳孔如平静的湖面,藏着与年龄不符的倔强和冷静,她缓缓道,“我只相信殿下你。”晏徽云听了这话,眉头仍未舒展,反倒皱得更紧。清殊心头一跳,有不好的预感。“圣上久病初愈,突发雅兴,召令各大臣陪同前往御临苑秋猎,你的兄长和父亲正在其列。”晏徽云脸色很不好看,“因此举突然,京中带兵的武官都要随同护卫,我家只剩府中几个护院。”清殊如坠冰窟,只觉得后背发冷。“甚么?全都走了……”她原本只是猜测有蹊跷,可如今连淮安王府都抽不出人,清殊心头疑云密布。一个是巧合,两个是巧合,接二连三就决计不是了。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能耐,将每个人甚至于皇帝都当作棋子,巧妙相连,制造出一个绝路。这样玄妙,这样神秘而可怖,心里头不对劲却偏偏说不出道理来,只能恨自己倒霉……这究竟是真的命运,还是人为的计谋?难道这就是姐姐的命运?这就是她自己的命运?!清殊眼中酝酿着风暴,想了很久,却又沉静了下来。她道:“那就请殿下就将几个护院借给我。”晏徽云还在思索对策,闻言皱眉道:“亭离山脉绵延,林子里多豺狼,几个护院顶甚么用?”清殊没再说话,四处看了看,径直往马厩跑去。她知道学堂里有人骑马上学,譬如眼前这位爷。“站住!你人没马高,几时学过骑马?”晏徽云随手一捞竟然没有抓住。小姑娘一阵风似的跑到马厩,一眼就认出熟悉的逐风。通体乌黑的骏马傲得很,打了个响鼻,铜铃似的眼睛眨了眨,好像也认出了清殊。“我自然不会骑马。”清殊坦荡直言,转而看向晏徽云,也不开口了,只一手拉着马鬃毛,一双眼直勾勾瞧着他。虽不说话,却也胜过千言万语,眼底意思很直白——会骑马的那个还不快过来。晏徽云挑眉,眼底有些不悦:“你使唤起我来倒很是自在。”他语气虽不大好,脚下却没犹豫,三两步上前,顺手把清殊一捞,安放在马背上,自个儿拉着缰绳。“园子里不好纵马,一盏茶的功夫出府,一个时辰穿过坊市出城。”清殊微微拧眉:“一个时辰?”“嫌慢?”晏徽云拉着马头也不回,冷道,“上回顾及你的小身板,逐风才提了五成速,你要是不怕,让它提个十成速,半个时辰也行。”清殊立刻道:“我不怕,只是你不用顺道回府叫上家丁吗?”晏徽云:“左不过几个废物点心,多一个少一个有甚么打紧?”听了这话,清殊也不再问了,她心里沉甸甸地装着事,脑子里也容不下旁的。只是……似乎漏掉了甚么?逐风都快离开学堂大门,她还没想起来,直到后头远远传来盛尧熟悉的骂声——曲清殊!小王八羔子,你把我落下了!!作者有话说:好久不见了各位,疫情期间请注意防护哦肉汤◎姐姐受伤啦◎好像陷在了一场幻梦里,浮浮沉沉,混混沌沌。最先闻到的是雨后潮湿的气味,再是药草的清香,不知是甚么品种,微苦清冽,似香非香。尚未清醒的神智,在某一刻的朦胧里,却抓住一丝熟悉的气息。清懿的眼皮动了动,有了些许知觉。“醒了?”有人嗓音沙哑。清懿本想看向说话之人,谁知只是轻轻扭头,浑身便散架似的疼。这痛感来势汹汹,叫她一时没防备,额头冷汗密布,要不是死死咬住嘴唇,必得痛呼出声。“疼就是疼,有甚么忍的?”说话之人轻笑出声,只是呼吸却并不如话语那般平淡,反倒像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带着几分轻喘。清懿察觉声音近在咫尺,余光望去,她这才看清周围的环境。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小山洞,不知是哪个动物辟出的巢穴,空间不大,只恰好能容纳一人躺下。她被安置在最里侧,身下铺着厚厚的树叶,身上盖着一件月白色的外袍。至于那个人……他身上的外袍不见了,此刻只着中衣,靠坐在山洞口。察觉到她的目光,也不必她开口提,这人便知道她想问什么。“这里是亭离山脉腹地,那匹疯马一径往险处跑,把你救下时我才发觉周围地势险峻。我的马前蹄断了,是已只能在原地等你家人找来。”外头天色渐渐擦黑,尤其是密林深处,更是黑得快。鼻尖尚能闻到潮湿的青草味,清懿大抵猜到当时的情形。她甫一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下过一场大雨?”那人点头:“是,在原地等了大半时辰还不见有人来,天就下起了大雨,你这副情形倘或再淋雨,那便无需我救了。”清懿闭上眼睛,语气淡淡,“哦,那多谢殿下搭救,原是不必的。”听她没有半分真诚的道谢,那人也不恼,反倒轻笑出声,“你这小气性,罢了罢了,是我非要行善积德,多行义举,不能劳姑娘一个谢字,回去以后转头把我忘了也是有的。”清懿原不想再理他,偏偏心里头生出些许火气,“殿下若是急于挟恩求报,也等脱险再议。您金尊玉体犯险救我固然可贵,时时挂嘴边儿倒落了下乘。”那人笑得更大声,还待说什么,却好似牵动了伤口,一时没了声音。此时天色昏暗,他半张脸藏在阴影里,叫人看不清神色,只余略微急促的喘息暴露出他的异样。清懿立刻觉察出不对劲,“你伤在哪里?”“没有伤。”他好像恢复了一点,又扯开嘴角,若无其事道。清懿也不再问,只凝神看向他,“袁兆。”这世上能这样称呼他的屈指可数,小门小户的姑娘直呼皇亲国戚的名姓,原该有被冒犯的情绪,可他却觉得无比自然。她这样连名带姓地叫,语气平淡得很,竟让他也有一丝熟稔感。袁兆回视她,笑道:“怎么了,我名字这样好叫?”这是暗指危机时刻,她也曾脱口而出一声“袁兆”,还有即将昏迷的前一刻,她气如游丝,呢喃着的一声“袁兆”。清懿不接这个话茬,淡淡道:“既然伤着就别装了,疼就是疼,有甚么忍的?”昏暗的光线里,林中树影摇曳。一个躺着,一个坐着。两个的视线在光影里交汇。率先移开目光的是袁兆,他闭了闭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才勾起嘴角道:“小姑娘何必这样聪明。”聪明得一眼看穿他故意逗她生气,好移开话茬,不让她发现他身上的伤。“伤在哪里?”她重复问了一遍。袁兆淡淡道:“左不过是胳膊折了,待回去以后请太医诊治,自然无碍。”清懿沉默片刻,没有答话。她强撑着直起身,胳膊才使了三分力,浑身磕碰出的外伤都在叫嚣着疼痛。“你要作甚?躺回去。”见她起身,袁兆语气里的散漫顿时一收,竟显出几分强硬。清懿不听他的,一手支撑着坐起,一手擦了擦额角疼出的冷汗,轻喘道:“伤在哪?你自己说,还是我来看?”轻轻浅浅的话语,却透露着不容置疑的味道。清懿从这个视角看去,才发觉袁兆的不对劲。他脸色太过苍白,绝不是折了胳膊那么简单。初看以为他闲适地靠坐在洞口,再细看,他分明是特意藏着伤口,不叫她这一侧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