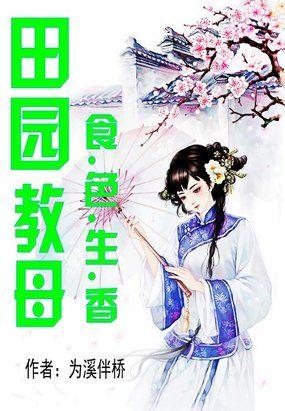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免费阅读全文 > 第108页(第1页)
第108页(第1页)
“椒椒。”清殊骤然回头,又惊又喜:“姐姐!”“嗯……”清懿勾起唇角,声音尚带着几分虚弱无力,目光却柔和,“这几天……是不是吓坏了?”清殊胡乱擦了擦眼睛,把眼泪憋了回去,又抓着姐姐的手蹭蹭脸,含糊道:“嗯,所以你以后不能吓我了,你去哪都要带着我,掉山洞掉悬崖,都要带着我。”“呸,又胡咧咧。”清懿笑容清浅,捏了捏她的脸。他们一行在寺庙里待了三日,这里的一应吃穿都由一个十来岁的小沙弥送来,至于那位老僧,只初时露了面,之后再无踪影。这个寺庙来历古怪,他们默契地没有探寻过任何违背常理的事情。比如,清懿受了极重的内伤,竟不出三日便好了大半;袁兆胸膛贯穿的伤口如今只剩浅浅的伤疤;就连清殊吸入瘴气后晕乎乎的后遗症也没了,神清气爽得很。谈心◎姐妹俩坦白啦◎再次回到府中,躺在柔软的床榻上,发梢带着沐浴后的清新,清懿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清殊累得睡了过去,发出规律的呼吸声。翠烟彩袖和碧儿几个大丫鬟这几日也折腾得够呛,见了清懿安然无恙,俱是狠狠痛哭一场,现下也被打发下去休息了。紫金蟠螭六角香炉里燃着沁人心脾的月沉香。室内未燃烛火,借着月光洒下的半点微芒,清懿的眸光里流淌着万千思绪,脑中还在回想这几日的事情。白日里,他们下了山后,长阶与高塔不知何时就消失了。待出了林子,发觉山中的三日之期,于外界而言不过一瞬。等候在外的陈平昌,见他们四人一齐出来,简直活见了鬼一般,还未来得及叫嚷,便被晏徽云眼神制止。“人已找到的消息不必传出去。”陈平昌虽不知为何,却不敢细问,领命而去。袁兆和清懿玲珑心思,转瞬便明白其中深意。袁兆:“你这一遭实在蹊跷,暂且瞒了消息,也好让幕后之人失了防备,细细查上几日,总有蛛丝马迹。”“我也正有此意,殿下既已替我开了尊口,倒免去许多麻烦。”清懿缓缓道,“救命之恩,再加上零零总总的恩惠,我们姐妹二人欠两位殿下良多。口头报恩的话不好再提,日后有能用的上我二人的,必定竭力偿还今日恩情。”她言辞恳切,话说得极妥帖,可是分明又将彼此界限隔开,讲礼得很。袁兆垂眸看了她一会儿,想说的话究竟是没有说,只淡淡道:“你伤及肺腑,一时半刻无法痊愈,在家好生将养罢。”清懿没有抬头看他,规矩地行了一个礼,又朝晏徽云福了福身。光阴倒转,前些时日里近乎生死相托的两个人,眼下好像又遥隔万里。陈平昌在晏徽云的指令下悄悄安排了马车,预备送姐妹二人回去。袁兆站在原地目送,始终没有上前。马车缓缓行驶的那一刻,清懿不经意瞥见他眼底的眸光,如沉静的寒潭,叫人读不懂其中的思绪。这个眼神,初初看来并没有甚么特别,可直到月上柳梢头的深夜里,却在清懿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亭离山上,她对着孔明灯祈愿的那个夜晚,他的眼神也是这样。克制而清醒,像是亭离山巅凝而不散的雾气。只是,那时的他又坦坦荡荡,笑着对她表明心意,仿佛内心冲破了无名的枷锁。而此刻,这道看不见的枷锁拦住了他,于是,他除了平静地看她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清懿歪着头,看了看熟睡的清殊,又给她掖了掖被角。谁知小丫头竟然醒了,懵懂道:“姐姐怎的还醒着?”清懿拍拍她的背:“把你吵醒了?夜还深着呢,你继续睡。”清殊听话地翻了个身,一时间室内又静了下来。清懿以为她睡了,过了半晌,小姑娘又扭头看向她,问道:“姐姐原先是不是认得袁先生?”清懿挑了挑眉,“此话怎讲?咱们不是一同在项府雅集上认得他的吗?”黑暗里,清殊狡黠一笑,还带着困倦的鼻音道:“少来,你还想骗我。若非故交,他怎会冒死救你?”“你不知道,我们过去的时候,长阶上的血迹还在,触目惊心得很。世子殿下说袁先生定然伤得极重。试问一个人在自身难保的情形下,还想着救你,怎会是萍水相逢,非亲非故呢?”清殊闭着眼,小嘴叭叭。“总是瞒不过你。”清懿静了片刻,无奈一笑,“只是,我从前认得他,他如今却不认得我。不过……这样也正合我心意。”“椒椒。”黑暗里,清懿的声音分外的柔婉,“我有许多事情也不知该如何告诉你。我与他,一两句话说不清。今日,他救我之恩我固然铭记,可我也只能记这一分恩情,不愿牵扯旁的。恩恩怨怨算不分明,索性一是一,二是二,囫囵带过不计较了。”“再者,我不愿多有牵扯,还有一桩因由。你只看他待人坦诚,行事仗义,又在你学里授课,他身上的皇家印记便淡了几分。你又向来是个不重尊卑的率性人,自然只认他人品贵重,略过他身后的煊赫家世。”清殊点头道:“自然是这样,一个人的德性顶顶重要,如若他家世寒微,却有高山仰止的品行,在我心里便是第一等。反之,他若是个朱门绮户里养出的草包,我多瞧他一眼都是不能的。”“原先我只当他是个寻常富贵公子,单有几分才情罢了,并不值当我敬佩。可如今来看,只凭他豁出命去救你这一桩,我便觉得他是个好的。”清殊钻进姐姐怀里侃侃而谈,“自然,我姐姐这么一个如珠似玉的美人,他若是因着一点儿私心才相救,也属常事,我并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