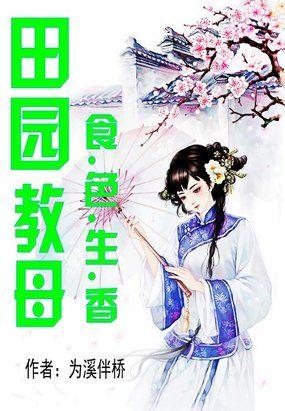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免费阅读全文 > 第143页(第1页)
第143页(第1页)
清殊虽没见过如此无理的要求,但还是从善如流又说了一遍,连个磕巴都不带打。王耀祖快气撅过去了,狗腿子赶忙扶住他。“快!快!把她抓下来!”王耀祖原地跳脚,声嘶力竭,“一个区区四品官家的女儿,竟然这么嚣张!我从未见过这么无礼的丫头!”侍童们犹豫着不敢上前,但是见自家主子快气成疯狗,只能畏畏缩缩地往墙边去。清殊有些意外,没想到王耀祖承受能力这么差?放现代连入门级都不算的垃圾话,居然快把他气晕,看来还是古人见识太少。“手都拿开,别碰我!”清殊一边躲闪,一边试探着爬下那边的墙。往下一看,墙体足足两人高,真摔下去那就应了自己说的话,变瘸子了!正心急时,冷不丁有人道:“下来。”熟悉的声音入耳,抬头看到来人,清殊结结实实愣住,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以及内心的沸腾——为什么偏偏这种狼狈的时候被他看到啊!为什么不干脆眼前一黑,晕倒算了啊!这个王八蛋学了隐身术吗怎么走路没有声音啊!清殊迟来的羞耻心狠狠作祟,肺都要气炸!晏徽云不知是甚么时候来的,此刻就站在围墙下,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由不得清殊犹豫,后面的王耀祖已经气得撸袖子自己上了,比起后面的恶心玩意儿,在晏徽云面前丢人也不算甚么了。“你你你站稳了,我跳了啊,别把我摔了!”清殊急得比划。“就你那几斤肉。”晏徽云连白眼都不屑翻,不耐烦地勾勾手,示意她快点。清殊深呼吸,心一横,往下跳。也不知他是如何动作的,清殊只感觉到自己被稳稳接住,在一个不算温暖的怀抱里待了片刻,然后双脚着地。短暂的接触间,她好像闻到了一丝极淡的香味。晏徽云的衣服从不熏香,也不佩戴贵族公子时兴的冷香玉坠。而这香味又如此熟悉,即便只是若有似无,清殊也分辨出来,那是菖蒲,杜衡混合着兰草的气味。他身上戴着那只香囊——两年前,清殊送他的生辰贺礼,绣工潦草简陋得不像话,却被贴身携带两年之久。清殊怔愣片刻才回神,突然想到自己还在生他的气,立马掉头就走。“站住,回来。”晏徽云揪住她后颈脖子,“有东西给你。”清殊被揪回来,后退时没站稳,不小心歪倒在他怀里,又很快站好,“干嘛?我跟你不熟,不要你的东西。”“这个也不要?”晏徽云打开匣子,里面盛着一堆品貌上佳的绯红色珍珠。清殊本想不屑地推开,待目光移到珍珠上就挪不开眼了。这是京城少见的顶级南珠,红粉色更是稀有。而现在,有一整盒摆在她的面前。这对于一个识货的珠宝设计师是多么极致的诱惑!短暂地思考了珍珠和骨气谁更重要的问题,清殊悄悄吞了吞口水,然后狠狠闭眼,“不要,拿走!”晏徽云:“?”他眉心微蹙,眼底罕见地闪过一丝凝重。连珍珠都不要了,看来事情真是越发棘手。在来之前,狗头军师晏徽容出了一堆馊主意,甚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屁话,他一句都不想听。最后只采用了投其所好的方式,反正他早就备下了礼物。只是没想到,姑娘这回是油盐不进,连以前十有九次成功的财帛贿赂都打动不了她的心。啧,难搞。清殊见他没话讲,头一撇,哼了一声就要走。晏徽云顺手将随身带着的短刃往墙上一戳,十来寸的长度,正好堵住她的去路。清殊:“??”她现在等于被晏徽云本人和晏徽云的刀堵在墙脚!哪里有人用刀拦人的?!哪怕他调整成了刀背向人,她也不会夸他贴心的好吗!清殊气晕,没忍住给了他邦邦两拳,“晏徽云你有病啊!不认识你就要砍人吗?我就不认识你,不认识你,怎么样?打我啊!”晏徽云敷衍地挡一下,见姑娘炸毛的样子,想了想还是觉得挨两拳让她解气比较好。于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奇观正在角落上演,世子爷面无表情挨打,等她拳头都红了,才问道:“好了没,我跟你说两句话。”清殊瞪大眼睛,她手都疼了,这人还若无其事,更气了!“说甚么说,以前没长嘴,现在也不用长了!”她愤愤,说着就弯腰想钻出去。晏徽云手一捞,把人逮回来,皱眉道:“你怎么生气生个没完?”清殊惊讶抬头,难以置信道:“你还有理叫我不生气?哈,真有你的啊晏徽云!”她气冲脑门,一刻都不想待了,下死力推开这人,结果他纹丝不动。“打了也打了,骂也骂了,听我说两句话就不行?”世子爷简直耗尽他这辈子的耐心,极力压制着火气在说话,语气甚至夹杂着无奈。“不听。”清殊不管不顾。两个人纠缠时,另一头的王耀祖绕了远路带着人追出来,他还没来得及惊讶是哪家登徒子捷足先登,就见一把短刃飞劈而来,擦过他头发丝,狠钉在树干上!“喂!你是何人?!敢动我的人,知不知道那丫头是我先看中的!”王耀祖气得声音都劈叉了。“滚!”一声暴躁至极的冷喝。“嗨呀,满京城还没有敢这么跟我王耀祖说话!我非要给你这个臭小子一点颜色看看不可!”王耀祖一而再再而三被人下脸子,再忍不了,原地捡了根树枝就要上去拼命。冲到一半,冷不丁那登徒子突然回头睨了他一眼,那眼神叫人遍体生寒:“别叫我说第三遍,滚。”“!!!”王耀祖寒毛都要炸开!淮安王世子晏徽云?我的天爷啊这个阎王怎么在这里!王耀祖虽然嚣张,但还是要命的!来不及思考对方的登徒子行为,他连滚带爬地溜了,临走前还抖着嗓子道:“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你们聊你们聊!”等世界终于清净,晏徽云才稍稍收敛起戾气,“你把东西收了,再听我说会儿话。”清殊左右出不去,就靠着墙扣手,垂着脑袋不看他。晏徽云当她默许,便把东西递给她,然后问道:“你是不是气我不辞而别?”清殊动作一顿,还是不抬头,嘟囔道:“我才不生气。”见她这副样子,晏徽云莫名想到产珠的蚌壳,也是这样嘴硬,轻易不肯以柔软示人。但是他恰恰拿这只蚌壳没办法。在世子爷我行我素的人生里,哪里跟人扭扭捏捏地解释过什么。误会不都是用拳头解决的吗,还需要啰里八嗦?可是现在,晏徽云闭了闭眼,开始啰里八嗦:“我是抗旨出京,那样的情况下,如果我说了,只会拖累你们家。”虽然自以为摆出了最温和的姿态,可在旁人看来还是一样面无表情。听着听着,清殊渐渐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垂眸,“那你为甚么一句话,一封信也不带给我?”见蚌壳开了一条缝,晏徽云微微松了口气,无奈道:“跟你个丫头片子说杀了几个人吗?便是我母亲和我姐姐也不曾接到过家书,我们家的男人没这个习惯。”清殊微眯眼,狠狠瞪他:“对!你说得对!犯得着和我说吗?我又不是你的姐姐妹妹,既然这样世子殿下也别再说了,你也不是我的谁!”听到她这句话,晏徽云脸色一沉。细究起来她说的也没错,可是偏偏就有种莫名的不舒服。清殊见他脸色冰冷,更不爽:“怎么世子殿下还不高兴了呢?生气的是我才对!”话音刚落,晏徽云突然问:“那你呢?你又为何不高兴?”清殊被问得一愣,懵了半晌,慌忙推了他一把,急急钻出去,“明明是我先问的,你不答话反倒来问我,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