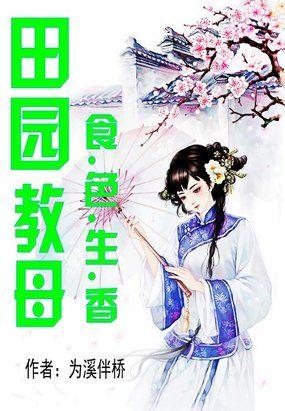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免费阅读全文 > 第174页(第1页)
第174页(第1页)
野草就该扎根泥土,不必攀附高枝。作者有话说:姐姐马上又要搞事业啦!二丫◎姐姐视察啦◎晨时,流风院。彩袖一早便忙活开,盯着小丫头们收拾箱笼,余光瞥见有粗心的落下了东西,顿时柳眉一挑。“小蹄子,昨儿吃酒了?昏头昏脑!”她对照着册子一一检视物件儿,少了的便打发人添上。原本惫懒的丫头这会子也精神了,不敢对付了事。有几个鬼精鬼精,推着玫玫出来顶缸。玫玫老实上前道:“彩袖姐姐,我晓得错了。”玫玫如今长高许多,只是照旧一副憨傻模样,十二岁的丫头心眼子倒比不上小的。“有你甚么事?姑娘的首饰盒子又不归你保管。”彩袖没好气地瞪她,然后目光扫过后面缩头缩脑的几个丫头,扬声道,“你们少在我跟前弄鬼,平日里躲懒倒罢了,这回非比寻常,四姑娘要回浔阳探望外祖,特特备了几车礼,你们敢丢三落四,仔细身上的皮!”小丫头浑闹惯了,知道彩袖面上利害,实则是个心疼人的,便团团围着她讨饶,缠得她脱不开身才罢了。听见屋外的笑闹声,翠烟打起帘子望了一眼,回身笑道:“姑娘你瞧,有彩袖在,四姑娘这一路上必然妥帖。你晚些去倒无妨。况且大少爷也会一同去,你安心了结手头的事要紧。”时值暑月伊始,清殊的假期旅游计划就已经开始施行。这个时代交通不便,从京城到浔阳,路上就要花费十天半个月,又加上女子出行不便,所以姐妹俩自五年前上京后,竟一次都没回过外祖家。这回正好赶上曲思行赴南边出差,恰好要经过浔阳,清殊便寻思着跟哥哥一起回去。清懿原本也要去,只是因着手头还有要紧事没有处理,才打发妹妹先走,她延后几天跟上。一切收拾停定,清殊却还磨磨蹭蹭不愿出门,歪在姐姐怀里嘟囔:“甚么事这么要紧?连同我一块回家探望外祖都要往后捎了?”清懿轻拍她的脑袋,嗔道:“小人家,自玩你的去,现下扮出不舍得我的样子,回了浔阳捉鱼摸虾,你就是野兔子回了山里,到处撒欢,哪里还记得我?”被点破心思,清殊哈哈大笑,“吧唧”亲了姐姐一口,被对方嫌弃地笑骂,“你这皮猴!”“好吧,那我先走一步,你不要太想我。”清殊背着自己做的随身小包,噔噔两步上了马车,然后又探头冲曲思行喊道,“哥,我们脚程慢些,正好一路游玩,又能等姐姐。”曲思行坐在马背,睨着她道:“约定驿站等岂不妥当,你打量我不晓得你的心思呢,由着你玩,我的差也不必出了,路上就得耗一年。”清殊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哥你真小气,大不了路上费用我包了,一应消费我曲四姑娘买单!”“哟呵。”曲思行差点被气笑,探到马车里捏住她的耳朵,冲清懿挑眉道:“你瞧,咱们四姑娘现在口气可不小,财大气粗的。”清殊笑弯了眼,故意道:“还不是哥哥姐姐教得好。”插科打诨间,众人哄笑。曲府车队在欢声笑语里启程,一路出城门去。-送走兄妹二人,清懿立刻备车往城郊去。袁兆留下的那个农庄位置偏僻,用来安置女子工坊再适合不过。经过数年的发展,这里已经被清懿打造得井井有条。织锦堂作为前端售卖窗口,吸引了不少高门加盟合作,拓宽了商品的出货渠道,也让它的名声越发响亮。而女子工坊作为后备生产基地,能为织锦堂提供稳定货源,相关制造技术与创新工艺也能得到保护,这也让织锦堂的货品更具有竞争力。经过数年发展,女子工坊分裂出不同条线,种类繁多,有制香、刺绣、纺织等等。女工们在这里制作的东西经由专人送往织锦堂旗下的各处商铺贩卖,所获利润按照章程规定分配,俨然形成了完整的雇佣体系。最开始的女工大多由流民组成,后因织锦堂名声大噪,吸引了不少穷苦百姓,因此规模越发庞大。四之有三的平民女子在工坊做活计,有的是临时工,有的是长期工,如若表现突出、工龄又长,在薪资待遇上便优厚些。女子工坊的发展像是蝴蝶煽动翅膀,初时看,众人只觉得是多了个做活计的庄子,也就是只招女子这一条稀罕些,旁的雇佣之法、奖惩体系,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等到时日渐久,不知不觉间,风气变了。从前只能依附男人生存的女子有了谋生的手段,家里多经济来源,变得富裕。与此同时,那些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猛然发现,自家婆娘性格越来越泼辣!原来忍气吞声的良家妇女们一个个都像炮仗点了火,再不做受气包。连京兆尹都抚着胡须叹息,这几年的休夫休妻案比以往多数倍不止!他白天忙着处理公事,晚上还要去岳丈家哄妻子,他家这位太太这几年因投资织锦堂赚了不少银子,一家子吃喝都叫她包了,便是打点上司都是花她的钱,京兆尹哪里还硬气得起来。正因如此,即便夫人一改往日贤惠本色,天天出去约人打马吊,他也不敢放一个屁。要命的是,昨儿他在气头上指责她“不守妇道”,转眼就被回骂得眼冒金星,人家扭头就收拾银票回娘家,他能怎么办,他只能屁颠屁颠地去哄!想至此,他头疼得饭都吃不下去。满京城,上至朝廷命官,下至贩夫走卒,像他这般头疼得不在少数。这几年,女人们做买卖的做买卖,进工坊的进工坊,一个个都尝到了自食其力的好处,哪里还肯过原来的日子,再受闲气,大不了和离走人!反正织锦堂能供她吃住!有织锦堂做靠山,女人们越发有底气,于是也更加忠心。许多人尚且没见过大东家的真面目,却打心底爱戴织锦堂这块招牌,它为所有女子提供了停靠的港湾。东街口的徐二丫正是受过好处的一员。二丫打小没了娘,长到十六岁,就被酒鬼老爹以两吊钱的价格卖给了西街的王二麻子做媳妇。王二麻子好赌又好色,打光棍到四十来岁还讨不到老婆,是个人见人厌的家伙。二丫自知嫁给他这辈子就毁了,于是终于硬气一次,在上花轿的头天晚上逃走。酒鬼老爹找了三天三夜,扬言只要她敢露面,就一根绳子勒死她这个讨债鬼。那时,她慌不择路地逃到城郊,躲在农庄薯窖里不敢出来,直到饿得奄奄一息才被庄里的妇人发现。那个妇人高鼻深目,异族人长相,却能说中原话,“不得了,这怎么藏了一个人?!”她唤来了另一个主事人,二丫迷迷糊糊睁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女子。后来,这女子成为了她的大掌柜,二丫也知道了她的名字,赵鸳。彼时,赵鸳用一碗米粥吊住她的命,问她来处,又问她将来的打算。二丫撑着气力给她磕了一个头,“谢姑娘搭救,我贱命一条,倘若您不嫌弃,就留我做个粗使丫头。倘若您为难,我明儿便回去,买包耗子药,让那老不死的见阎王!总之我必不会遂他的意!”赵鸳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搀她起来,待她躺好才道:“我既不留你做丫鬟,也不叫你去买耗子药。”“那是何意?!”二丫瞪眼。赵鸳这才微勾唇角:“寻死算甚么本事,真厉害,就去他眼皮子底下,好好活给他看。”自此,二丫开始跟着赵鸳做生意,学出几分名堂,她便自个儿支了一个摊子,正正就坐落在东街口!按赵鸳教的,酒鬼老爹再来闹时,二丫比他更横,一张断绝父女关系的文书直接甩他脸上,随后就是一柄苕帚劈头盖脸地砸,再吵将开,她就往官府衙门敲冤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