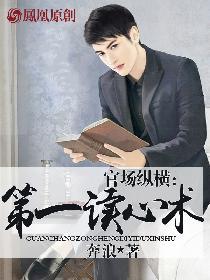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关于你的那些岁月txt > 第4页(第1页)
第4页(第1页)
“媳妇儿,你在干嘛?”严信的声音从画面外传来,低沉磁性,带着笑,温柔得能掐出水来。女人没抬头,敷衍地回了句:“工作。”画面晃动起来,从她的正面拍到了侧面。看得出,严信举着dv坐到了旁边。女人埋头工作,画面呈静止状,隔了一会,又听到严信的声音:“媳妇儿,你看我一眼。”女人扭头瞥了一眼,回头继续敲键盘。几秒后,严信又说:“你再看我一眼。”女人面无表情,对着镜头白了一眼。“你到底要干嘛?”下一秒,画面一晃,变成粉蓝一片,不动了,只听女人惊呼一声,接着是严信咯咯的笑声:“你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吃掉!”女人:“滚开,小流氓!”严信:“美人儿,来给爷香一个,爷会对你很温柔的~”……陈希雯仓皇地关掉了视频。面红耳赤,心跳如雷。她看到了严信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极尽温柔,极尽宠溺,充盈着爱和欲。这六年来,严信绝口不提那个女人,一次都没有,她渐渐报以侥幸心理,以为他已经放下。可这间充斥着蓝色的办公室,桌上的相框,不愿摘下的戒指和始终不变的袖扣,还有这些照片和视频……太多的细节足以证明,她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严信从未放下。那段感情,贯穿他整个少年时代,他视若珍宝,珍藏至今,根本不可能放下。陈希雯陷进沙发里,闭上眼睛,用力摁了摁眉心。罢了,他放不下,换她放下好了。她倒要看看他能撑到何时。庆功会的地点在钱柜最大的总统包,立信律所几十号人齐聚一堂,灯红酒绿,欢歌笑语,笑闹拼酒摇骰子。唯一人,脸黑成锅底,坐在角落一语不发,呈冰山状。大伙见小老板全程冰块脸,都不敢来招惹,唯独周子安不怕死,一屁股坐到旁边,顺手搭上他的肩。“小信信,你这是干什么,拿了奖应该开心才对嘛。”他刚才走了一圈,脸上两坨酒精红,笑起来欠嗖嗖的。严信冷冷地翻他一眼。周子安痞笑:“来ktv是大家举手表决的,不是你说管理要人性化吗。况且,他们也不知道你唱歌五音不全啊。”“你闭嘴!”严信斜眼:“举手表决怎么不叫我?我不是人吗?”“你是老板,只管出钱就行了,谁还管你啊!”见严信脸更黑了,周子安递了杯酒过去,讨好道:“哎呀,顺应民心嘛,来,喝杯酒消消气。”严信盯着酒杯,一伸手,捞过来干了。周子安正欲表扬,自己手中那杯也被他夺过去一口闷掉了。严信把杯子递回去:“你可以滚了。”周子安啧啧两声,道了句“牛逼”,闪人了。两杯纯的威士忌一下肚,严信顿觉口舌干涩,胃里烧得慌。几个胆大的见小老板喝酒了,也纷纷跑过来敬酒,嘴上巴巴儿地说着“立信威武”,律助小唐连什么“千秋万代,一统江湖”都喊出来了。严信不好推辞,一一应酬着又灌了几大杯。七年前,他仗着醉酒发过一次疯,自那之后便发誓戒酒,这些年来几乎滴酒不沾。这一通喝下来,不光胃烧得慌,连身上也滚烫发热。包间的洗手间被不知哪个喝高了的人占了,严信等了一会,抬脚往外走。他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凉水浸湿皮肤,稍稍降了些温,被酒精染的酡红消退后,反倒显出一丝苍白。严信摁着太阳穴走出洗手间,不经意抬眸,身子猛然一僵。走道的装饰绿植旁,站着一个背影娇小的女人,马尾辫,发梢微翘,宽松的白t恤,牛仔裤,双腿笔直修长。女人懒懒地靠在墙上,右手垂在身侧,指间夹着一支烟。严信想都没想,径直走过去,按住她的肩扳了过来。一张娇俏动人的脸,睫毛又浓又翘,眼线勾上了眉梢。“抱歉,认错人了。”严信转身就走,刚迈出一步,衣袖被拽住。他回头,脸上表情匮乏。“帅哥,你搭讪的方式out了。”女人笑得很媚。严信笑不至眼,淡淡道:“你觉得我需要搭讪吗?”女人抽着烟,上下打量他一眼,瘪嘴:“看来你确实认错人了。”严信:“还不算笨。”女人一怔,咯咯笑:“既然如此,不如将错就错,如何?”严信勾了下嘴角:“我也不笨。”说完,抽出手,转身走了。身后传来女人娇滴滴的笑声,溶在ktv嘈杂的音乐声中,渐渐消散了。刚进包房,就听到小唐高八度的声音——“哎哟哟,钱柜就是牛逼啊,这个月刚出的新歌,歌单里就有了!”记录员lda凑过去看。“什么歌啊?”“《真相是真》!”小唐手指一戳,优先播放了。lda:“诶,你这不厚道啊,把我的歌顶掉了。”“乖啦,等下重新帮你点。”小唐飞了个吻,三步化一步跑小舞台上去了。严信找了个角落的单人沙发坐着,大理石桌面上,几个玻璃杯里装着颜色各异的不明液体,他选了杯蓝色的,一口干掉,酒味很淡,甜到发腻。旁边的果盘七零八落,他瞅了半天,勉为其难叉了块西瓜。音乐声起,小唐捧着麦克风摇头晃脑的唱,像个百老汇歌手,声情并茂,很是陶醉。严信瞅她那样,乐得笑了一声。视线扫到大荧幕滚动的歌词上,渐渐的,表情在脸上凝固,整个人像是沉入几万米的深海,胸腔被挤压着,痛苦得快要窒息…………林宇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家老板。他是严信钦点的律助,这一跟,就是两年。在林宇的印象中,他们家小老板二十有四,年轻有为,虽然偶尔玩游戏时会犯下孩子气,但绝大多数时间是成熟稳重的,尤其是工作状态下,冷静理性达到了非人的程度。可现在的画面,诡异得令他浑身哆嗦。小老板……哭了。确切地说,他正默默流泪,那眼泪珠子跟不要钱似的,一直掉。林宇看得眼皮直跳,蹑手蹑脚跑去找周子安。周子安正跟几个合伙人划拳,“二十”刚喊出口,一只手被拽了回去,对面那人笑得拍大腿,连喊几声“喝酒”。“靠!”周子安愤然回头,瞅见愁眉苦脸的林宇,一挑眉:“什么情况?”林宇小声道:“周律师,你去看看小老板吧。”周子安:“他怎么了?喝醉了?”林宇皱眉摇头,手挡嘴凑过去说:“他哭了。”周子安:“……”周子安把严信架去了隔壁空包房,途中不少人担忧问怎么了,周子安挥手说没事,让大伙继续。进了房间,严信仰面瘫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房间没开灯,仅靠着外面走道昏暗的灯光,却依然能看清他脸上湿漉漉一片。周子安坐到旁边,抠了抠额头,问:“你怎么了?”严信沉默着,眼泪止不住地掉。他不懂,为什么那些歌词像是把他和她的时光通通写尽,那些开心过、痛苦过、纠缠过,如今只能缅怀的时光,全都被写进了歌里,一字一句,割肉剜心。那些被压抑的思念,如潮水,排山倒海。他来不及挣扎,瞬间被淹没。周子安静了一会,沉声问:“想她了吗?”他没有说“她”的名字。自她走后这六年,严信怎么过来的,周子安很清楚。他绝口不提她,用工作麻痹自己,全年无休,不让自己有一刻放松,绷得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皮筋。她的名字如同禁忌,一旦说出口,他必然崩溃。严信仍旧一语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