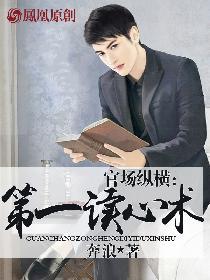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暗恋泰剧多少集完结 > 第12页(第1页)
第12页(第1页)
这人是谁?是他听见陈云杉名字的第一反应。
“我想帮你治病。”再见时,陈云杉挺诚恳的对他说。
陆铭灏则反问:“你是慈善家吗?”
这简短的对话之后,陈云杉只给了他半天时间考虑,或许都没有半天,他下午再一次的敲开了他家那扇门,陆铭灏看了看陈云杉,又看了看自己桌面上摆着的那束散发出香气的纯白的百合花,咬咬牙,决定从这困境中逃出去了,就算陈云杉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困境中,他也认命了。
陆铭灏算不上利己主义者,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摆在自己面前,不接住了,那就是傻子,所以在逃出生天的机会和微不足道的自尊之间做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前者。毕竟自尊那玩意在过去的几年中,早已被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的践踏。
他记得自己坐在陈云杉那辆开往北京的豪华车的副驾驶上还在想:如果这具残破的身体被对方相中了的话,那他大概也可以做到。
不过他下一秒看了眼车窗反射出来自己那张过于颓丧的脸时,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这个样子,谁愿意多看一眼?要钱没钱,要脸没脸,腿还是瘸的,陆铭灏直接打消了自己过于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上,三个多月的相处下来,陈云杉对自己很尊重,甚至是过于周道。
在北京,乃至全国的骨科大夫基本上都带他见了个遍,治疗方案谈了好几个版本。这人平时的工作本来就不轻松,经常加班,所剩不多的闲暇的时间基本上都拿出来为他在研究这些,还要担心他是不是住得惯,吃得惯,找了好几个护工和厨子让他选到底哪个用着最顺手……林林总总的好,又让陆铭灏捡起了来时路上那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又在这人眼中看不出任何的**,陆铭灏开始相信这人真的是个正义的慈善家的设定,他完全是有钱没地方花,有爱心没地方安放。
正因此,陆铭灏才会不断的挑战陈云杉的底线,看他到底能容忍自己到何时。
“来吃饭。”陈云杉再次进来时,周遭已经没了运动的气息,而是伴着一股食物的香气的居家感。
陈云杉走到他的面前,见他没动也并不觉得意外,只是在准备放着面和果汁的餐盘放在床头柜上时,看见他喝空了的酒瓶子和酒杯,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陆铭灏等着陈云杉的说教,谁知他却没说什么,只是道:“麻烦你收一下那个酒瓶子,我这东西没地方搁了。”
陆铭灏伸手把酒瓶子拿起来,随手放在地上,陈云杉把食物放好,对他说:“快尝尝吧,第一次做,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然后满是期待地看向他,就像一个等待老师夸奖的小学生。
这眼神有点熟,陆铭灏也想不起自己在哪里见过,他懒得去想,看着面前摆着的食物——一盘喷香的葱油面,上面摆着几棵翠绿的青菜和一个形状完美的流心太阳煎蛋,还有一杯鲜榨的橙汁。
陆铭灏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破坏了完美的摆盘,把食物放进嘴里,每根面条都裹着浓重的葱油香伴着酱汁的鲜美,味道着实还不错,但他没说,只是在陈云杉的注视下三下五除二的吃完了一盘子面,喝光了杯中的橙汁。
陈云杉嘴角噙着笑,就像考试得了一百分,在他放下筷子的时候,对他说:“今天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大夫说很重要,所以希望……”他的声音停顿了一下,眼睛看向床头柜边摆着的几个空酒瓶子,说:“你能少喝点酒,因为某种药物可能会在酒精的作用下失效。”
酒精,是陆铭灏的好朋友。
在他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还稍许能给他带来一丝丝的快乐。这种快乐很短暂,却能让他忘记家庭的破败,妻离子散,一步步跌进没有未来的深渊的过程。
“当然了……”见他没回答,陈云杉又把话收了回来,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对他说:“一天一杯也不是不可以,等一会儿回来,我们可以去酒庄买些高品质的红酒,这样可以助眠,你看怎么样?”
“随便吧。”陆铭灏吐出自己常说的三个字,毕竟,有酒总比没有强。
“嗯。”见他答应了,陈云杉笑着端着盘子离开了。
这次陆铭灏没有再去看窗外,而是盯着陈云杉从自己房间离开。
他感谢陈云杉带给他新生的希望,可他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同学之间都是呼风唤雨前呼后拥,谁想竟然因为家庭变故迎来迎头痛击。这种从天堂跌到地狱的人生经历,更让他明白有些施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陈云杉这样一味不求回报的付出,就是傻子都会清楚这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