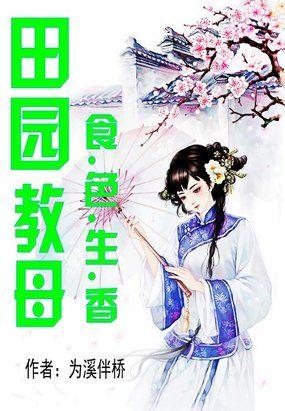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被迫嫁给了父亲的仇敌 都关月 > 第39页(第1页)
第39页(第1页)
宁嘉徵不再继续这一话题,而是找出了那纸曾经令爹爹烦恼不已的婚书,当着奚清川的面撕了个粉碎。“奚清川,我与你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这婚约就此作废。”“奚清川,我与你拜堂成亲属实是迫于无奈,做不得数,我从不是你的娘子。”奚清川悔不当初,他便该早些享用宁嘉徵,不该容许宁嘉徵守孝三年。假若他早些享用宁嘉徵,三年的功夫足够他将宁嘉徵调教好,而今只消他勾一勾手指,宁嘉徵便会自觉自愿地张开双腿。骤然被碎纸片洒了一身,他不由感叹自己对宁嘉徵过于心慈手软了。见宁嘉徵不言不动,他以为宁嘉徵姑且放过他了,岂料,宁嘉徵复又提起了剑来。宁嘉徵修为尽废,幸而招式记得一清二楚。他以一招“月上重华”,在奚清川身上划出了无数道口子。当年,奚清川便是以“月上重华”陷害爹爹的。发泄了一番后,他定了定神,上得喜榻,望向穷奇,紧张地道:“你且上来吧。”——纵然他并非心甘情愿,但他既已答应了穷奇,断不会食言而肥。穷奇爬上喜榻,端端正正地坐好,继而将右爪搭在少年手背,郑重其事地问道:“吾从未与人或是兽交过尾,倘使有所差池,望你不吝赐教。”穷奇这姿势教宁嘉徵想起了缠着小妹玩耍的“王不留行”,登时忍俊不禁。见少年笑了,穷奇歪着毛茸茸的大脑袋,困惑地道:“吾所言有何可笑的?”宁嘉徵解释道:“你这副样子不像是在向我求欢,而像是想同我一道玩耍。”穷奇认真地道:“吾从不玩耍。”——自打出生起,他便随父亲一道东征西战,全然不知何为玩耍。宁嘉徵信手摘了一只喜球来,往穷奇一抛。穷奇下意识地接住了喜球。宁嘉徵摸着穷奇的脑门道:“真乖。”穷奇吐出喜球,低吼着道:“吾可是上古凶兽,不是寻常的猫狗。”这低吼丝毫不能让宁嘉徵生出恐惧,他淡然自若地捡起喜球,再度抛向穷奇。穷奇的神志尚未反应过来,嘴巴已经抢先一步叼住了喜球。宁嘉徵莞尔道:“你果真喜欢玩球。”穷奇觉得他作为上古凶兽的威严受到了挑衅,一爪子将喜球四分五裂了。宁嘉徵便又拿了只喜球来,抛予穷奇。穷奇第三次接住了喜球:“……”宁嘉徵取笑道:“口是心非。”与此同时,他在心里感叹道:终于有毛茸茸愿意同我玩耍啦!穷奇一掌将喜球拍扁,接着道:“吾曾见过大家闺秀抛绣球招亲,这喜球若是绣球,吾接了喜球,便是你的夫婿了。”这话说得平铺直叙,不含心悦之情。宁嘉徵本就不认为穷奇会对自己一见倾心,遂好奇地道:“你为何要我委身于你?”穷奇不假思索地道:“因为你是吾见过的最为特别的凡人,且吾未曾体验过交尾的滋味。”宁嘉徵这才坦白地道:“我亦未曾体验过交欢的滋味,谈何赐教?”“吾听闻交尾能令人如登极乐,是以,你如若舒服了,便是吾并无差池;你如若难受了,自是吾出了差池。”穷奇将喜球的“尸体”一扫,继而扑倒了宁嘉徵,一字一顿地问道,“凡人,告诉吾你姓甚名谁。”——毕竟是初次交尾,他自然甚是重视,必须知晓交尾对象的名字。“我唤作‘宁嘉徵’,‘安宁’的‘宁’……”宁嘉徵突然说不下去了。“嘉徵”意寓着“美好的预兆”,而他……他眼前霎时尽是那些锥心刺骨的旧事,方才同穷奇玩球的欢喜荡然无存,直觉得自己将被灭顶。便在此时,穷奇的嗓音刺入了他的耳蜗:“‘嘉徵’的意思是‘美好的预兆’吧?”他心脏一紧,面无表情地道:“这名字与我并不般配,我分明是凶兆。”穷奇思及先前宁嘉徵所言,猜测道:“你认为奚清川之所以做下那些事,皆是因为你?”宁嘉徵颔了颔首:“我十岁那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奚清川逼着我爹爹订下了他与我的婚约。爹爹一直想毁去婚约,他便栽赃嫁祸害死了爹爹;师兄们相信爹爹清白无辜,他便诛杀了他们;娘亲与小妹可作为拿捏我的工具,他便当着我的面伤害她们,还将她们囚禁了;为了让我绝了回重华楼的念头,他烧毁了重华楼;生怕我报复,他剜出我的内丹,碾成了齑粉。我害人害己,当不起‘嘉徵’之名。”穷奇不解地道:“你为何要将他人的罪孽归咎于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