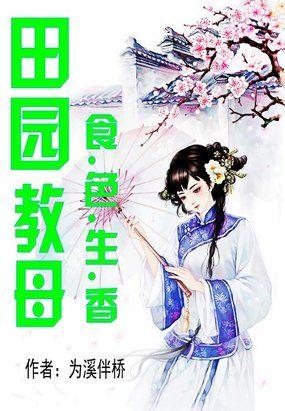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被大佬盯上后我红了笔趣阁 > 第8页(第1页)
第8页(第1页)
“简老师,我们先对哪场戏?”
简浔愣神之际,叶贺阳已经翻开剧本,小声的询问他。
“就这段吧,沈父病逝入殓后,沈沐阳收留三月的第二天,得知沈沐风半夜带走大半家产,站在梨树下出神这里开始。”
简浔走到窗户边,默念了几遍台词后放下剧本,等着叶贺阳入戏。
阳光男孩紧跟邻家男孩的步伐,迅速走到邻家男孩找的场景,看了一眼窗外的细雨朦胧,闭上眼。
再次睁开时,眼里再无光点,面无表情的透过薄纱似的雨雾看向远处,时而眨眼睫毛扑闪,没有灵动,只有经历太多无奈的沧桑感。
简浔挪步到他的斜后侧,满眼都是身前全身都在诉说着悲凉的沈公子。
“公子,雨大了,回屋吧。”
叶贺阳余光扫了一眼察觉到他的视线而慌忙低头的简浔,突然有些想笑,他嘴角勾了勾,却怎么都扬不起来。
“三月,梨熟了,我想尝尝。”
简浔挪开了小心翼翼的眼神,毫不犹豫踩在旁边的凳子上,两步跨上窗台,抓住窗棂回头看着双眼依旧无神的叶贺阳。
“公子,一个够吗?”
所有的美好都该属于他
剧本的这里,沈沐阳还在出神,三月识趣的摘了两个黄澄澄的梨,下滑一步,跳下梨树站到公子面前。
他捧起衣角用力的擦干净梨上的雨水,掏出小刀要削皮。
沈沐阳抬眼悠悠开口:“别麻烦了,切两半吧。”
三月点点头,手起刀落,梨子一分为二,露出白玉般细腻的果肉,诱发出沁人心脾的甘甜。
沈沐阳接过,看了一眼三月留下刀刃痕迹的手心,“我送你的不是这把刀。”
三月条件反射的按了按胸前,又惊恐着松开,“那刀太贵重了,小人……我不敢乱用。”
公子不喜欢府里的人用这种自称,不论是贴身的两个护卫,还是刚进府一日的自己。
他觉得生命平等,上天给了他富庶优越的家境,自然就收走了最让人无能为力的生命力。
都说沈父走后,公子烧纸都没掉过泪,入殓时更是面无表情,一言未发。过后也是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仿佛过去的日子从未有过父亲这个人。
可是,三月知道,不是这样的,半月前他站在台下看戏的样子,比在戏台上唱独角戏的自己,看起来还孤独。
后来,他一路跟随着走到幕后的小破屋,目光坚定的看着三月,“梨子成熟了,能帮我摘吗?”
那次,三月拒绝了。
再后来,戏台下每日都会有沈沐阳的身影,不管天晴下雨,不管台上有人无人,他都会安静的站在同一个地方蹙眉,不知是在想什么。
就在昨天,他又荒谬的跟在三月身后到了小破屋的门口,说出口的还是那句话。
“梨子成熟了,能帮我摘吗?”
不远处就是他的护卫,三月不明白,摘个梨而已,哪里会差人到用自己,但是长久以来,他次次看戏次次给钱,可以说,他是自己能没被饿死的直接原因。
为唯一的观众乃至救命恩人做点并不为难的事,是理所应当。
“沈公子,我随你去。”
转身收拾头面的空档,三月瞧见沈沐阳破碎了筑起的心防,眼里的悲痛几乎快要将他压垮,泛出眼角的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般往下掉。
世人都说,沈府出了两个大“孝”子,沈父逝世时,老二在赌场红光满面,沈父逝世后,老大冷漠无情,一滴泪都不见流。
不过是具劳累不得的躯体,不过是满府的奴仆需要这份生计养活一家老小,不过是还要撑起摇摇欲坠的沈府所有,不过是外人眼里的不屑与中伤,不过是对生命的消失殆尽无能为力……
他落泪的那一刻,三月觉得所有的美好都该属于他。
他不该是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他比很多人都要热血,也无人会比他更让人觉得安心。
藏在里衣夹层里的短刀很贵重,是人情,是冷暖,是要藏好的心思,也是要断掉的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