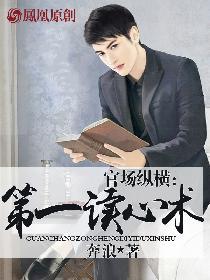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时刻新闻 > 3 答案(第2页)
3 答案(第2页)
一股热浪冲上来,席卷住她,程刻抵在她身体深处释放。前奏温缓,尾声潦草,她把话说了出口,两人都没了心思。尤时从他怀里起来,径直去浴室冲洗。
出来的时候程刻在阳台抽烟,真稀奇,快十年了,她从来没见过他抽烟。尤时坐在沙发上倒水喝,他跟着过来,把烟掐了。尤时才注意到他抽的是她的烟。
他凑到她身旁,呼吸间有淡淡的薄荷烟香。程刻吻着她的头发,低声说:之前一直想试一下你抽的烟什么味道,刚刚试了一下,味道不太浓,但你还是少抽吧,对身体不好。
他声音有些沙哑,未褪的情欲和烟草揉碎在一块儿,他每一句话都说得缓慢。
也别节食了,你已经很瘦了,太瘦对身体不好,还不好看。
他的吻落到她唇上,轻而又轻的。
为什么又推开我?
尤时平静地说:我以为我早就告诉过你答案了。
他抱紧她:尤时,我不想这样。我不想
我来宜城,确实是为了你,但也不全是为了你。这几年,我也很累了,不止是你想休息,我也需要休息。
你不应该来找我的。程刻。
我只是想待在有你的地方。
尤时脸上闪过一丝痛苦,几番欲言又止,最后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她看到了他放在沙发边上的背包。
程刻捧住她的脸,温柔地亲吻,舌尖细细描绘她的唇形。尤时仰着头,没有推开他。
许久,他松开她站起来,提上包,对她说:一小时后的票。我该走了,你照顾好自己。
但是尤时,我回不去京都了。
木质门轻声合上,尤时在沙发上发了一阵呆,才拿起烟盒。烟盒还是他打开过后的样子,打火机一明一灭,她将烟点上,吸入一口。她仰起头,吐出一串烟雾。
她并非烟不离手的瘾徒,香烟对她来说是调解情绪的物品,但程刻在的这两天,她抽烟的频率一再飙高。尤时心里想着事,险些被掉落的烟灰烫到手,她忽而笑出了声,笑自己自欺欺人。
将近十年的时间,她看似在不断往前走,却始终被困在原地,等待他出现,捡起支离破碎的她。
手机提示声响,她捞过来看,是日历提示声今天该给家里汇钱了。
年底辞职回家时,父母都高兴,他们希望她留在县城老家,找一份按部就班的工作,早点结婚生子,后来听到她要去迎州,当即和她吵了一架。与其说吵架,不如说是他们单方面的输出,这种时刻她向来都没话说。她自作主张到京都上学是,留在京都工作是,甚至来迎州也是,每做一个选择都不被祝福不被支持,她已经习惯了。
他们歇斯底里好些天,最后尤时与他们约定,每个月固定给他们汇钱,他们才妥协。她家里还有一个刚上高中的弟弟,要用钱的地方多得是。
她好像过上了十六七岁时梦寐以求的生活了,经济上不愁吃穿用度,有独自远行的能力,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于是她与家庭挣扎,与自己挣扎,与现实挣扎,毅然决然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原来,她已经离十七岁这么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