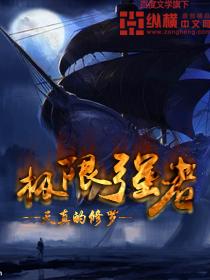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西方的没落看不懂 > 第115章(第1页)
第115章(第1页)
&ldo;艺术科学&rdo;总是依附于各别艺术领域无时间的、概念性的界定,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证明问题的基础根本没有受到冲击。艺术是活生生的单位,活生生的东西是不能被分割的。博学的学究们首先做的常常就是把无限广袤的领域分割成由完全表面的媒介和技术标准所支配的局部,然后赋予这些局部永恒的有效性和不可变换(!)的形式原则。他们就是这样来把&ldo;音乐&rdo;和&ldo;绘画&rdo;、&ldo;音乐&rdo;和&ldo;戏剧&rdo;、&ldo;绘画&rdo;和&ldo;雕刻&rdo;分割开来。再接着,着手界定绘画&ldo;之&rdo;艺术、雕刻&ldo;之&rdo;艺术等等。但事实上,技术的形式语言不过是实际作品的面具而已。风格并不是肤浅的桑泊(seper)‐‐算得上是达尔文和唯物主义的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种东西,即材料、技术和目的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艺术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是形而上秩序的一种揭示,是一种神秘的&ldo;必须&rdo;(t),一种命运。它与不同艺术的物质界限毫无关系。
因此,要是依据感官印象的特征来对艺术进行分类,就会在阐述中曲解形式的问题。因为我们怎么可能设定一个&ldo;雕刻&rdo;种类具有如此普遍的特征,以便承认从那一特征中可推导出普遍的规则呢?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什么是&ldo;雕刻&rdo;?
再说到绘画。根本就没有绘画&ldo;之&rdo;艺术这种东西,只要比较一下拉斐尔的基于轮廓线之作用的素描同提香的基于光和阴影之作用的素描,就不会觉得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如果认识不到乔托或曼特尼亚(antegna)的作品‐‐是由笔触所创造出来的浮雕‐‐与弗美尔(verer)或戈雅(goya)的作品‐‐是在涂满颜料的画布上创造出来的音乐‐‐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就不可能把握更深刻的问题。至于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和拉韦纳的马赛克,甚至都没有技术手段上的相似性可把它们归于所认为的同一种类,在蚀刻画与弗拉&iddot;安杰利科(fraanli)的艺术之间,或在原始科林斯式的瓶绘与哥特式的教堂窗户之间,或在埃及的浮雕与帕台农的浮雕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呢?
如果说一种艺术真的有边界的话‐‐它的心灵的既成形式的边界‐‐那也是历史的而非技术的或生理的边界。艺术是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体系。根本没有一种艺术门类可贯穿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甚至在(例如在文艺复兴的情形中)所谓的技术传统暂时地欺骗我们相信古代艺术规则具有永恒有效性的地方,也根本上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在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中,没有什么东西与多那太罗(donatello)的雕塑或西纽雷利(signorelli)的绘画或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正立面有任何关系。本质上,&ldo;十五世纪&rdo;(attrocento)是与同时代的哥特风格而不是其他东西有关。古代希腊的阿波罗类型是受到了埃及肖像画或早期托斯卡纳的埃特鲁斯坎墓穴绘画的表现方式的&ldo;影响&rdo;,这一事实所意味的东西恰恰就是巴赫利用外来的主题创作赋格曲的事实所意味的东西‐‐他表明他能用那一主题来进行表现。每一个别艺术‐‐中国的山水画、埃及的雕塑或哥特式的对位音乐‐‐都是曾经存在的,它将随着它的心灵和它的象征主义的消失而一去不复返。
二
有此认识之后,则有关形式的概念便告豁然开朗。不仅技术工具,不仅形式语言,而且艺术门类的选择本身,都被看作是一种表现手段。一件杰作的创造之于个体的艺术家来说‐‐《夜巡》之于伦勃朗或《纽伦堡的名歌手》之于瓦格纳‐‐所意味的东西,正是某一种类的艺术的创造,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之于一种文化的生命史所意味的东西。它是划时代的。除了最纯粹的外部因素,每种这样的艺术都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个别有机体。它的理论、技术和传统全都分享有它的特征,且不具有任何永恒的或普遍的有效性。当这样的一种艺术诞生的时候,当它走完其生命历程的时候,它究竟是消亡了,还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为什么这样或那样的艺术在某一特殊的文化中是主导,或为某一特殊的文化所不具备‐‐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意义上的形式的问题,恰如为什么个体的画家和音乐家无意识地回避某些阴影和和声,或相反,显得特别偏爱某类阴影和和声,以致作者的特性就整个地根基于此,这是形式的另一个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性尚未被理论、甚至当今的理论所承认。不过,恰恰是从这个方面、从艺术的观相的方面说,艺术是可以理解的。迄今还有人认定‐‐对认定所涵盖的重大问题不加些许的考查‐‐在传统的分类框架(其有效性是想当然的)中被详加说明的几种&ldo;艺术&rdo;是一切时代和地点最可能的艺术,如果在特殊情形中缺乏其中的某一种,乃是由于偶然缺乏创造性的个人、必需的环境或伯乐式的赞助人去指导&ldo;艺术&rdo;走上它的&ldo;正轨&rdo;所致。在此,我们所采取的乃是我所谓的把因果原则从既成的世界移至生成的世界的做法。如果对于活生生的东西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对于它的命运及其可能的表现和独特发生的必然性毫无洞察力,人们就得求助于实在的和显见的&ldo;因果&rdo;来建构他们的艺术史,因而这种艺术史必将是由一系列仅仅表面一致的事件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