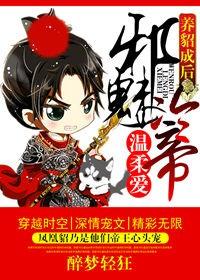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西方的没落看不懂 > 第125章(第1页)
第125章(第1页)
巴罗克绘画的情形因为下面的事实而进一步复杂化了,那就是,它还包含了一般的大众感受与更敏锐的感受性之间的对立。欧几里得式的可感知的一切也是大众的,因此,真正的大众艺术都是古典的。基本上说,正是大众艺术的这种大众的感觉特征,构成了它对于浮士德式的才智之士而言难以言喻的魅力,使他们不得不去为自我表现而斗争,不得不通过艰苦的搏斗来赢得他们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对古典艺术及其内容的沉思是纯粹的新生:在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为之斗争,一切都自由地自行提供。同类的某种东西,也被佛罗伦萨的反哥特倾向获得了。拉斐尔在其创造性的许多方面都显然是大众的。但是,伦勃朗不是,也不可能是。从提香开始,绘画变得越来越富有性爱的色彩。诗歌也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哥特式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性爱的‐‐但丁和沃尔夫拉姆就是明证。欧克赫姆和帕勒斯特里纳的弥撒曲,或巴赫相关主题的作品,是一般的会众所无法理解的。普通民众是由莫扎特和贝多芬培育出来的,他们一般地把音乐看作是视某人的心境而定的东西。自启蒙时代发明&ldo;为全体的艺术&rdo;(artforall)这个短语以来,音乐厅和剧场便影响着人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程度。但是,浮士德艺术不是&ldo;为全体&rdo;的,且本质上也不可能这样。如果现代绘画不再对任何人而只对少数(且人数一直在下滑)的爱好者有吸引力,那是因为它抛弃了对连大街上的人也能理解的事物的描绘。它把现实的性质从内容转向了空间‐‐根据康德的看法,只有通过空间,事物才能存在。并且,随同那困难一起,形而上的要素已经进入了绘画,这个要素不会对门外汉妥协。相反,对于斐狄亚斯而言,&ldo;外行&rdo;这个词根本没有意义。他的雕刻完全是诉诸于实体性的东西,而不是诉诸于精神性的视觉。一种没有空间的艺术先天地是形而上的。
七
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原则。在一幅绘画中,把事物无机地相互叠置或并列在一起,或是前后排列而根本不重视透视或相互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本不强调它们的现实性对空间结构的依赖‐‐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这种依赖的否定‐‐这样做是可能的。原始人和儿童在他们的深度经验把他们的世界的感官印象或多或少引入某一基本秩序之前,就是这样画画的。但是,这种秩序在不同的文化里依据这些文化的原始象征的不同而有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如此自明的那种透视法的创作,乃是一个特例,其他任何文化的绘画对它既没有认识,也不打算认识。埃及艺术选择以迭加的行列来再现同时发生的事件,由此减少画面视角的第三向度。阿波罗式的艺术把人物和群像分开安置,故意回避在再现的平面中出现时空关系。波吕格诺图斯在德尔斐的奈达斯礼厅(lescheoftheidians)的壁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没有任何背景去把各个场景联系起来‐‐因为这样的背景会对下面的原则形成挑战:只有事物是现实的,而空间则是非存在的。埃伊纳神庙的山墙,弗朗索瓦巨爵(fran&edil;oisvase)和帕加马的巨人檐壁饰带上众神的排列,全都是没有有机特征的、分离的和可相互变换的动机按波形合成的方式创作的。只是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出现了连贯系列的非古典的动机[帕加马祭坛的忒勒福斯(teleph)壁画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例子]。在这个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情感是真正哥特式的。它实际上把群像的组合引向了如此完美的高度,以致它的作品仍是后来所有时代的典范。但是,群像的排列全都与空间无关。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就是色彩斑斓的广延在光阻(light-resistances)自身之内创造的一种无声的音乐,理解的眼睛能把它当作事物和生存加以把握,能从一种看不见的颤动和节奏行进到距离中。由于这种空间排列,由于其不知不觉地以空气和光的透视取代了线性透视,文艺复兴本质上已经被打败了。
现在,从文艺复兴在奥兰多&iddot;拉索和帕勒斯特里纳那里的终结一直到瓦格纳,从提香一直到马奈、马雷(arées)和莱布尔(leibl),伟大的音乐家和伟大的画家一个接一个蜂拥而出,而雕塑艺术却整个地变得无关紧要了。油画和器乐朝着哥特风格所理解而巴罗克风格所实现的目标有机地发展着。两种艺术‐‐是最高意义上的浮士德式的艺术‐‐在其风格的限度内都是原始现象。它们有一种心灵、一种观相,因而也有一种历史。并且在这方面,它们是仅有的。雕刻从此以后所能实现的,只是在绘画、园林艺术或建筑的阴影中的少数美丽而偶然的片断。西方的艺术并不真正需要这些片断。不再有绘画风格或音乐风格的意义上的雕塑风格。根本没有连贯一致的传统或必然的统一性把马代尔纳(aderna)、古戎(goujon)、普杰(put)和施吕特尔(schl&uul;ter)的作品联系起来。连列奥纳多也开始公然蔑视凿子:他至多只是承认青铜铸件,且是出于其绘画般的长处的缘故。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米开朗基罗,对于后者来说,大理石块仍是真正的要素。不过,甚至米开朗基罗在老年也不再能有成功的雕塑,后来的雕刻家的伟大再也不是伦勃朗和巴赫意义上的。毫无疑问,他们有聪明的和有趣味的表现,但没有一件作品是&ldo;夜巡&rdo;或&ldo;马太受难曲&rdo;同一水平上的,没有东西像这些作品那样能表现全人类的整个深度。雕塑艺术已经脱离了文化的命运。它的语言现在再也没有意义了。在伦勃朗的肖像画中所具有的东西,在一件半身塑像中根本无法传达出来。就在这时和此后,时常也会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雕刻家,像贝尔尼尼或同时代的西班牙派的大师们,或像毕加尔(pigalle)和罗丹(rod)(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实质上超越了装饰的范畴而达到伟大的象征主义的水平),但这样的一位艺术家常常显见地或是文艺复兴迟来的模仿者,例如托瓦尔森(thorwaldsen);或是冒充的画家,例如乌东(houdon)和罗丹;或是一位建筑师,例如贝尔尼尼和施吕特尔;或是一位装饰家,例如柯塞沃克。并且其现场的表现,只是更清晰地显示出,这门艺术已无法负载浮士德式的重负,故在浮士德式的世界中已不再负有任何的使命‐‐因而,它也不再拥有一种心灵或一种具有特殊的风格发展的生命史。相应地,在古典的世界里,音乐是那种失败的艺术。最早的多立克风格可能是其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开端,可到爱奥尼亚风格成熟的世纪里(公元前650~前350年),它不得不让位于两种真正的阿波罗艺术,即雕刻和壁画;由于拒绝了和声和对位法,它由此不得不放弃作为一种更高级艺术的有机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