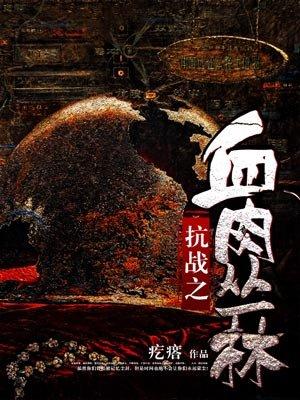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东京旧梦剧透 > 第187章(第1页)
第187章(第1页)
“你咬我作什么!”
“不是你让我咬的嘛!”
沈常乐缩回手来,见自己臂上又添了两道牙印,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将对方处理好的脚腕放在清凉的溪水中稍作浸泡,上了止痛和生肌的药散,再用绷布包扎妥当,才又背着人往城里走去。
路上冯友伦实在是饿极了,在树上顺手摘了两个野果,也顾不得酸涩难咽,擦了擦便往嘴里啃。
“喏,这个给你,算谢谢你救命之恩。”冯友伦伏在沈常乐背上,递了剩下的一个果子给他。
沈常乐就着他的手啃了一口,立马呸地吐了出来。
“这么酸?”
“浪费,你不吃我吃。”
“……喂,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沈常乐忍不住问。
“嗯?”冯友伦没心没肺地又咬了口果子,“也没什么,我爹非买了个官儿让我去当,我不肯,就跑出来了。”
“当官是好事啊,为什么不肯?”
“那怎么行!又不是我自己考来的,如何能心安理得。”
“世道如此,有什么关系?你不买,也自然会有其他人去买。”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反正不一样!诶……你是没瞧见那些个寒酸书生,一本一文钱啊!怎敢去买他们苦读十几载得来的机会。”
“夫子教过的,君子应……应……”冯友伦越说,声音越小了下去,“咦?那一句怎么背来着……我……我给忘了……”
啪嗒一声,果核落地,沈常乐回头一瞧,人竟是耷拉着脑袋睡着了。
宁相忘终于赶回了自家门前,可还没等他跨进那简陋的小院,便瞧见了当中被踩踏得东倒西歪的菜地。
“娘亲!”宁相忘目眦欲裂地推开房门冲了进去,却在瞧见屋里的情形时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破旧的木桌旁,一共围着八九个大汉。宁相忘认得他们,几乎都是洪老身边的人。他们此时每人手中端着一盘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直到一双木筷从当中伸出来,在其中一人手上夹起一块鱼肉,宁相忘才反应过来应该是他家桌子太小,放不下这些许东西才会如此。
他又往前挤了挤,才看清了桌上的情形。
木桌虽已缺了好几块角,可似乎刚刚被人用心擦拭过,干净得一尘不染。桌边一左一右坐着两个人,右边的是他娘亲,左边的却是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再张嘴,啊——”左边的男子耐心地将手里的白粥吹凉了,再用勺子一口一口递给坐在他对面的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