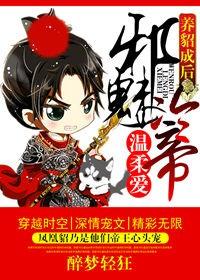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金风玉露全文免费阅读三水居士 > 第7页(第1页)
第7页(第1页)
就这样,你追我躲,跑了整整一条街,最后总算把人堵在一个深巷里头。魏王看着前头的死路,他年少领兵,这还是头一次碰上“穷途末路”的窘境。这时,徐宝璋已经追上来。只看少年喘着气道:“这下子,你就算喊破喉咙,都没用了!”金风玉露(六)眼看着徐小公子眯着眼大摇大摆地走来,那神似地痞流氓的架势,让李云霁下意识地退了又退,直到背靠着墙,无路可退为止。他回神来的时候,面前这胆大包天的少年已经伸手“啪”地一声压在墙上,将堂堂魏王困于方寸之间。徐宝璋抬眼瞪来,气势汹汹地问:“你为何一看见我就跑?”只看跟前的男人别过眼去,喉结咕咚地无声一动,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模样。徐宝璋拧了拧眉,偏过头去看他,这男人便又把脸转向另一边。两个人左看右瞧,转了半天,直教徐宝璋转得头都晕了,两手猛地固定住那个人的脸:“你别转了行不行,我眼睛都花了。”之前说过,楔尻之间也有大防,可徐小公子被家中长辈当正经男儿养大,而他秉性率真,不懂防范避嫌,只可怜了咱们的“老”皇叔李云霁,冷不防地被逮个正着。他怔怔地看着这近在咫尺的精致小脸,霎时,那近阵子不断出现在午夜梦回之中的异香如潮拢来——徐宝璋猛地被人推开了肩,他踉跄地退了一步,就见跟前之人做了个擦鼻子的动作,胸膛起落的速度比一般时候都来得快。“你……没事罢?”少年一脸担心地凑过来,魏王调整鼻息,此时,眼角的余光瞥见前方的拐角处,有一道鬼祟的影子。李云霁目光一厉,越过徐宝璋,直朝那头追去一看,那人影也遁得飞快,待李云霁赶来,就已经消失无踪。魏王看了看眼前的空巷,踩出一步时,察觉到了异状。他俯下身来,将那东西捡了起来——那是一条狼牙链,想是那人逃得太急,不慎落下。“——你怎么又跑了?”后头的少年追上来时,李云霁忙将链子藏进袖子里。徐宝璋就看眼前人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人突然也不跑了,却径自站起来走出巷子。少年急忙跟上:“哎,我等你等了这么久,你明明都来了,为何躲起来不肯见我?”“你看你想跑都没找对路子,莫非,你真的不是京城人?”“奇怪了,你为何要一直戴着代面,你是在躲什么人?”“我问了你这么多,你为何都不应我一声啊?”少年左一句“为何”,右一句“为何”,这么多的问题一下子抛过来,且不说李云霁一时半会不知如何解释,他又天生嘴拙,索性就一概不答,扭头直走。却说,魏王喜静,少年一路叽叽喳喳,饶说一般人,王爷早就拂袖一个提气,把人给甩下了。所以说,俗话说得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旁人都插不了手。然而,李云霁始终不发一语,到底还是惹得少年心头不快,道:“你一句话都不说,难不成你真是个哑巴?”此话甫出,前头的人顿然止步。徐宝璋一顿,轻喃道:“你……莫非……”真的不能说话?魏王静默不言,良晌,仿佛是轻叹了一声,然后便负手自顾自地走了。少年愣愣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跺了跺脚,恨不得掌自己的嘴:“瞧瞧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哎,你等等我!”李云霁没想到那少年又急追上来,只听他着急地在后头道:“对不住对不住,我、我瞎说话,恩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小弟确实无意冒犯——”徐宝璋虽说嘴急犯错,可到底懂事乖巧,自知错误,便诚恳道歉,这已经比许许多多明知冒犯他人,又恼羞成怒,还自觉自己不过一句玩笑话,是对方气量狭小的人好得多。见李云霁步伐稍缓,徐宝璋急匆匆抢步,挡在他的前头。便看少年揪了揪袍角,带着几分小心地抬头,问:“你不想理我,是不是因为……你很讨厌我?”魏王一怔——这小子怎么会这么想?他、他岂会,厌恶他……徐宝璋接着说:“要是,你不厌恶我的话,那你为何都不肯看着我呢?”少年仰着脸,就看男人缓缓地将脸转向自己,那滑稽的陶面后,一双黑漆漆的眸子映着周遭的灯火,好似藏匿着千丝万绪,教徐宝璋一见,就毕生难忘。徐宝璋回神后,露齿一笑,道:“算上方才那一回,恩公你一共帮了我两次,我阿爹说过,做人当饮水思源,知恩图报。”遂拂了拂袖,朝男人躬身拜道:“小弟徐宝璋,在此谢过恩公两次相救,请恩公受小弟一拜。”少年姿态大方端正,正是大家公子从才有的风仪。李云霁忽然受了大礼,忙伸手将徐宝璋扶起,却看徐宝璋嘻嘻一笑,说:“俗话说,相逢即是有缘,不知可否告知小弟恩公大名?”世间路人千千万,这个人三番两次救了他,可不正是有缘么?眼前的少年肤色如雪,一张小脸蛋圆润好气色,周围彩灯如炬,更映得那看着自己的明眸清澈灿亮,直教人不可逼视。见男人沉默不动,徐宝璋忽然想到,对方无法开口,正思量当如何的时候,魏王便伸来手,将少年纤细的手腕盈盈一握,执手到眼前。“你……”徐宝璋怔了一怔,跟着他就见男人稍稍俯下身来,那双睫毛浓密似羽,微垂的眼睑遮敛不住那双眼不自觉流溢而出的暖光。李云霁执着那白玉般的手掌,只觉好似握着这世间最柔软之物,让人不自觉就小心翼翼起来。他敛了心思,手指轻轻划在那摊开的掌心上。繁花如锦,皇宫里满园春色。太子侧妃所住的太宸宫里,一个少年公子凭栏而坐。春风送拂,日头正好,他不跑出去,反是看着自己的手掌发愣。就看他捏了一下手心,紧接着再放开,短短一盏茶的工夫,就重复了好几遍。此时,宫女搀着一个身怀六甲的女子走来。她额心点着梅花印,妆容精致艳丽,头戴六三只金步摇,姿态雍容,通身高贵气派。一见少年,她便会心一笑,道:“弟弟老盯着自己的手,难道,真能看出一朵花来?”“姐姐!”徐宝璋一回头,见到太子侧妃,猛地想起宫中规矩,急忙站起来。侧妃却将他的手揽来,拉着他坐回去:“此处没有外人,圜圜用不着在姐姐面前装乖。”徐宝璋道:“我以为姐姐去跟贤妃娘娘请安,不会这么快回来。”一旁的宫女说:“娘娘不日就要临盆,贤妃娘娘已经免了主子的请安了,让主子在宫里安心待产。”徐宝璋睁大眼,忍不住喜道:“姐姐这么快就要生了?”听到少年的稚言稚语,宫人都不由掩唇而笑。侧妃戳了一下弟弟的脑袋:“本宫都揣着这颗球九个月了,还快?”徐宝璋每隔一阵子方入宫一次,自然没察觉到日子过得飞快,太子侧妃自去年七月有喜,到现在可不正要生产了。徐宝璋看着那圆隆隆的肚子,不由想到数年前,阿爹快要生产的时候,那会儿阿爹的肚子可比娘娘这个大得多了,折腾得他亲爹站都站不起来,那一阵子只能躺在床上。侧妃问:“又在发什么愣?”徐宝璋醒过神,说:“圜圜只是在想,姐姐这肚子里的,是个小公主还是小皇子。”不等娘娘开口,大宫女就说:“徐公子不必猜,娘娘肚子里的,肯定是个小皇孙。”“锦瑶。”侧妃开口一唤,大宫女脸色微变,连忙噤声。侧妃抚了抚肚子,冲徐宝璋笑着道:“圜儿与其关心姐姐,不如想想来日,会嫁给什么样的男子,为他生儿育女。”徐宝璋到底是个尻子,年纪也不算小了,是该琢磨一下终身大事了。他听到“生儿育女”,脸陡地一热,讷讷道:“圜……圜儿,才不嫁人呢——”跟着又说,“圜圜要留在家里,孝顺父亲和阿爹!”宫人听了,又是一阵窃笑。徐宝璋看着她们,一脸困惑:“姐姐们都笑什么?”侧妃就明了自己这幼弟尚不通人事,家里也未曾请嬷嬷来教导他,是以连尻子有潮期这么重要的事也似懂非懂。于是,她也不想吓唬弟弟,便道:“这些话,你回去告诉你阿爹,听一听他怎么说。”徐宝璋见她们一个个都卖关子,哼了哼说:“好,弟弟回去问问阿爹,再来和姐姐们理论。”说罢,便站起来,向侧妃娘娘告退。娘娘照旧赏了他几样宫中的点心,便叫人送徐公子出去。少年离去了之后,侧妃身旁的侍婢便跪下来:“奴婢方才失言,请……请娘娘责罚。”侧妃看也不看她一眼,淡淡地道:“算了,下去罢。”宫女千恩万谢之后,便退下了。侧妃娘娘抚着肚子,她就快要生产了,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动气。再说,那宫女说的也不错。如今太子的两个侍妾都抢在她前头生下一子一女,她这肚子里的,非但得是个小皇孙,还当是个楔子,这样的话,待太子迎娶正妃时,她母子二人在这后宫里方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