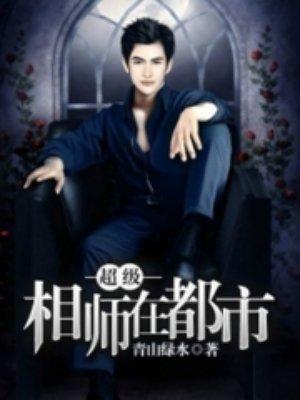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云影棠云清辞完整版阅读攻略 > 第270章 所谓平心静气(第2页)
第270章 所谓平心静气(第2页)
云清辞凝视她,眼底的情绪太强烈,怜惜,懊悔,心疼,恐惧,深刻的影棠头皮发麻,情不自禁后退。
他伸手,五指擦过药瓶,连同她的手一并握住。
胳膊传来巨大的牵制力,影棠眼前全黑,须全须尾被他淹没在怀中。
“病不讳医。”他声音嘶哑的,每吐一个字,喉管混音越重一分,犹如野兽鲜血淋漓,死亡黏住喉管的哮鸣。
“我们现在飞京城,去协和,北医,你的问题才出现不久,是早期,治疗及时,几个月就好。”
影棠缄默。
果然。
她的猜测成真了。
与把脉时薄颐章的凝重神情不同,他询问的表象,特征,影棠全没有。
甚至这段时间,她感到久违的精力,源源不断支撑着她东奔西跑,脑力消耗。
就算有疾病,追溯到保胎针的影响,也与欧洲报道的病发征兆,相去甚远。还有白瑛一直密切关注这点,时不时询问她身体感受,变化。
稍有怀疑,就联络京城导师,或者咨询她认识的知名主任。
再者,影棠并非不爱惜身体的人。保胎针有问题,千真万确。她不可能当真疏忽大意,原本也准备待明天落地欧洲,先做一整套体检。
云清辞察觉她抵抗态度,“不想离开香江?”
影棠挣脱他。
云清辞跟着她回到客厅,想到内地林娴姿风波未平,她自然要坚守在这儿,不添乱,也安心。
“那我们去养和。”
影棠脊背一僵,望着云清辞,愈发严肃,冷淡。
莫实甫就住在养和,这个关头她明目张胆在他眼皮底下转,查的还是身体。
莫实甫如何想。
是她认为林娴姿必胜无疑,忍不住翘尾巴,拿远东医药的事刺激他。
还是觉得云清辞在隐晦提醒他?
“我不去。”
云清辞浓眉紧皱,他并无压迫性靠近的动作,气势却比以往更凶残。
是强悍的暴戾,狂性,不容置疑的霸道,刹那铺张开。
显然,他要独裁了。
影棠悚然大惊,条件反射跳起来就跑。
耳侧劲风疾速,她感觉肩膀被巨力抄起,双脚离开地面。
与此同时,云清辞手机响起,他丝毫没有接听的意向,锁抱紧她,大步往外走。
影棠心跳狂乱了,拼尽全力的挣扎,“我可以去医院,你先告诉我什么病。”
窗外天色越发沉,乌云完全遮蔽了这座城,正午时分有了夜幕降临的阴暗和危险。
云清辞呼吸像黑暗里蛰伏的毒兽,很长时间才有一次,凝固的,沉滞着无法描述的东西。
“你的肝和肾——”他眼底一霎席卷骇浪,铺天盖地狂涌倒灌而出,挤占的空间翻腾,颠倒,“受损严重,初步估计,像慢性肝衰竭。”
话音未落,他手机铃声再响。
影棠脑子混乱,非是为薄颐章的诊断,她需要一个理由,拖过今天。
“你先接电话。”她看向书房,雪花白的大理石地板上,丢着云清辞的药瓶,“按时吃药,我想跟你平心静气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