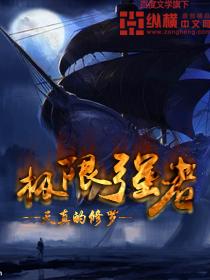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秋千索的三个基本意思 > 第160章(第1页)
第160章(第1页)
虬须大汉却忽出一脚踩在我手上,拾起我指尖前咫尺之距处的小小画筒,从画筒里抽出一张纸,张口念着纸上的字:蝶戏夕雾图。
我央求他,把画还给他。他矮下身,将画面于我眼前晃了一晃,而后一点点撕碎,自我的头顶洒下,犹如片片雪花。
那是十一年前,临渊哥哥送我诸多物什中,我唯一留下之物,却被他当成杂碎生生毁了。我怒瞪着他,恨不得切下他的爪子。
秋儿声嘶力竭地唤我,她极力想要挣脱束缚,可车夫把她死死拽着,以她的力气,根本挣不开。
虬须大汉用脚蹍我的手,他冲我大吼,命我不许瞪他,我手上吃痛,当下收回目光,他果真停了动作,不及我松气儿,腹上重重一脚,我下意识一捂,顷刻,猎靴雨点般踢在我身上。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未遭殃及,我几乎痛晕过去,好在秋儿一直唤我,我才咬紧牙提起神,不至晕厥过去。
秋儿苦苦哀求,虬须大汉始终不罢手,不知过了多久,虬须大汉终于停下,而我已经疼得无法动弹,身上皮肉浑如刀剐一般,口中鲜血如涌,眼睛睁也不开。
意识逐渐游离之时,我听到车夫问虬须大汉,我是不是被他打死了。
虬须大汉闻言又使劲踢了我一脚,我当真是再动弹不了,他骂骂咧咧,斥我太不能抗打。
我用尽力气睁开一丝缝隙,看到虬须大汉走到秋儿身旁,两个人犹如两堵墙,将秋儿围在其中。秋儿面若死灰,双瞳放大,神情极度惊恐,她用尽全力,做着微乎其微的挣扎。
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我应该听秋儿的,应该听秋儿的。
我尽力睁开的一丝缝隙终究撑不住了,耳朵里只有秋儿撕心裂肺的喊叫,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意识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剧痛中,溺亡之前,我仿佛看到了临渊哥哥,他鲜衣怒马,向我走来……
浑浑然醒来,周身如冰封血,冷意渗入骨髓,我睁开眼睛,却是风雨如磐,画卷被雨泡湿,支离破碎地散在我面前,纵然有心想拼,拼得了碎纸,却拼不回画景了。
原来是梦,原来不是梦。
我动了一下,钻心的疼痛立即从全身各处袭来,混沌的意识骤然清醒,当下仰起头目寻秋儿,却见秋儿一动不动地躺在雨里。我赶紧爬到她身旁,扯过散在地上的衣裳给她盖住,她身体冰冷如雪,肯定冻坏了。我唤她,她没有应声,我又使劲地摇她,她依然纹丝不动。
我瞬间慌神,如此场景,太熟悉不过。
不敢往下想,我咬牙撑身,试着去拉她,想要将她拖出这条阴森可怖的小巷,奈何手上浑不着力,软似棉花。
我放下秋儿的手,挣扎着站起身,靠在墙上,艰难地朝外走去。
我需要帮助,可是路上空无一人。我想找医馆,四周却尽是居宅。命运之手似乎在将我一点点推上末路。
走出巷子已耗尽我仅有的力气,再也无法迈进一步。而腿上的力气像是突然被抽空,支撑不住摇摇欲坠的身体,摔倒在地。
悔恨如一把铁锤,重重敲在心上,我不该轻信于人,该听秋儿的。
我蜷起身子,双臂横抱,好冷好冷,雨越落越大,我忍不住地颤抖,耳边似乎飘来秋儿的责怪,我不停地跟她道歉,对不起,秋儿对不起,都怪我,都怪我……
逐渐地,雨落成雪,我置身雪地之中,白茫茫没有尽头,垂眼望去,蔽体的是单薄夏裙,眼前飞雪肆卷,耳畔寒风呼啸,我张嘴大喊,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浑身上下,只有逼人的寒,挫骨的冷,风雪贴面而过,似锋刀般刮地脸生疼。
雪地一望无际,我不停地往前走,走了很久很久,久到遍体麻木,却始终看不到尽头。
大雪之中,忽闻人声,我回首一顾,身后雪地陡然不见,俨如虎狼的疼痛疯狂扑来,双眼一睁,雨停了。
周围立了一群人,对着我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