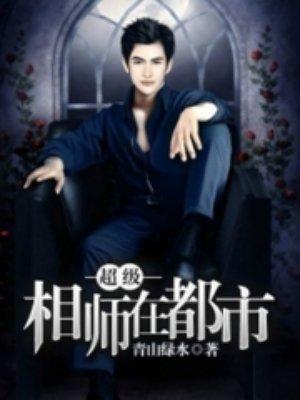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艾德里安同人文 > 第31页(第1页)
第31页(第1页)
诀别沿幽寂的小径往西走,走过二、三十分钟,越过一片莽茂的丛林,便可以看见缓斜的屋顶。停在梧桐旁,静视片刻,安德烈仰起头。彼方是白昼的天,无云也无鸟儿飞过,它白得空无一切,就像是黑夜单调的反色。而在脚下、身周,无论石路还是草木,均是浑黑的黑色,黑得噬尽了所有,只留下剪影般的轮廓。这反常的景象,令安德烈不由加快了步伐。最终,他如愿走出小林,矮缓的山坡间,小屋依旧安然地坐落在那儿,风起微动。镇定下来,走近。篱笆门从内上锁了,安德烈伸手越过,扯开栓。忽然,他呲起了嘴,栅栏上的木刺划破了他的手指。艳红的血,汩冒出一滴、两滴……安德烈挤挤伤处,将污血挤尽,于是,更多的红血顺着掌心指腹蜿流而下,坠在栅栏上,染红了草。可恶,伤口分明看着不大。左手捂住右手,压紧伤口,但只暂缓过一、两秒,指缝再次蹿红……就在这时,耳畔响起了陌生的声音:“该死的纳粹!你的死期到了!”“忏悔吧!可惜上帝已来不及垂听!”“……”风越吹越烈,唾骂声不知是从何处传来。屋前?屋后?屋内?还是屋外?“谁?!”“是谁在说话?!”环顾四周,依然是那廖寂的郊景。“艾德里安……”恍然记忆起,艾德里安已不在此处。他已经离去,离开了小屋,离开了他。他在寻找他,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只好只身返回此地,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小屋。“艾德里安……艾德里安……”撞开栅栏,踩过院里莽生的杂草,安德烈快步走向小屋。血越渗越多了,在黑白两色间添上了浓艳的十年走近,画面明晰了起来。半敞的窗畔,风将纱帘吹鼓成弧形的波浪,静悄悄地拂动。过滤过的阳光,此时既不灼目,也不浅淡,它裹挟着树叶的碎影落入,将这一方空间,映衬地好似山林中的精灵洞穴。安德烈眨眨眼,收回目光,将视线投向了厅室的正央。在那里,沙发靠背的边缘,可以瞥见一抹金麦色的发。那人稍稍换过了一个姿势,发上的浅光随之偏移。空气里,出现了翻动书页的声音。“安德烈。”他捻住书签,夹放在敞开的那页,仰头,眸子里含带着笑意。“你在看什么?”见安德烈没有回应,眉间攒出细小的褶纹,嘴角勾翘了起来。他歪着脑袋,注视着他。“艾德里安。”“嗯?”他忍不住抬手,抚触他的面颊。他笑了,将书完完全全地阖好,覆盖上他的手背,亲吻他的掌心。不够,仍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