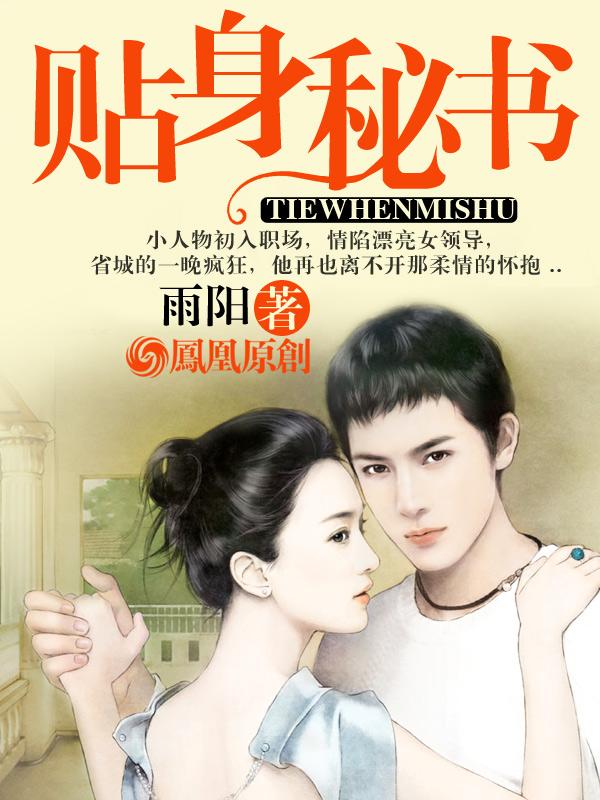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复仇的兽人rpg安卓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ldo;还不到时候,不好说啊。&rdo;片山耸耸肩。
在五楼下了电梯。门口站着两个腰插手枪的警卫,由于埃莉茄事先告诉过片山了,所以,他每人塞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
面对着电梯门是一条走道,两边排列着许多单间,埃莉茄一直将片山带到走廊的最左端。从那儿朝边上一拐,又走进了另一条走廊,与迎面走来的一对刚完事的男女擦肩而过,男的象是美国人,女的则是不折不扣的法国人。两边墙壁上没有一扇窗,在这条走廊的中部左边,又出现了一条小走廊,从右边数第二个房门,便是五百二十二号。再往左隔着两扇门便是摩洛哥女人的房间,而亚洲姑娘的房间就在斜对面。
埃莉茄从里面锁上门,踢掉脚上的高跟鞋,然后全身一丝不挂地钻进了没有门的浴屋,旁若无人地擦洗着身子。片山坐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点着了一根烟,那顶牛仔草帽挂在了架子上。这时,埃莉茄从浴屋中走了出来,边走边用浴巾在两腿之间轻轻擦拭着。
&ldo;你也脱了吧,我给你洗。&rdo;她扭动着腰肢。
&ldo;我还没有这种兴致,给我跳个舞吧,嗯。&rdo;片山回答道。
埃莉茄打开收音机的开关,合着节奏强劲的音乐,激烈地扭动着臀部和腰肢。片山吸完了一支烟,抬手示意埃莉茄可以停止了。
&ldo;怎么?还没有情绪?&rdo;说完,埃莉茄横躺在沙发上,将手搁在片山裤子的拉链上。
&ldo;妈的,混蛋……&rdo;
片山抬手照着俯身卧在沙发上的埃莉茄后颈部用力劈了下去,虽然,为了不至使她颈骨折断,片山用力时掌握了分寸,但埃莉茄依然一下子失去了知觉。片山用小刀将被单撕碎成布条,迅速捆住了埃莉茄的手脚。他又将剩下的两根布条做成绳套。接着他拔出手枪,顶上子弹,并按下了保险。他从埃莉茄的手提包中摸出这间屋子的房门钥匙,戴上帽子,把门拉开了一条细缝。他倾耳听了一会儿,又露脸观察了一下,走廊里空无一人。他来到走廊上,从外面将埃莉茄的房门锁上,从上衣襟内掏出头部呈钩状的两根钢丝。用这两根东西,他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摩洛哥女郎的房门,在特种部队必须掌握许多技巧,包括这种非法的技巧。
片山悄悄地闪进屋子,弯下身子,手拿绳套,左手伸向背后,悄然无声地关上了房门。床上垫褥被抛在了地板上,上面的中等身材的东南亚人正在责备底下的女人。那女人仰面朝天躺着,她背下垫着枕头,用头和颈部支撑着整个身子的重量,嘴里不时发出痛苦而甘美的呻吟声。两人都是一丝不挂。那男人的手枪插在枪套里,挂在墙上。
大凡人都具有第六感觉,即便有人从背后悄悄接近,要是距离过近,一般都能发现,至少有所感觉。但是片山经过无数次实践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一种过硬的本领,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到别人的身边而不被发觉。此刻,他犹如幻影一般,来到两人背后,用绳套勒住男人的脖子,猛地朝后一拽,生生把他俩给分开了。那男人倒向一边,片山又朝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目瞪口呆的女人的肋腹就是一脚。这一脚简直要把那女人的脾脏都给踢炸了,只见她哼哼两声,便昏死过去。
那男的被绳套死死勒住脖子,欲喊无声,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双手往外拽绳套,同时胡乱地伸出两脚朝片山乱踢乱蹬。片山轻蔑地冷笑着,就在那家伙抬腿的一霎那,他飞起一脚,正中他的下身,睾丸无疑被踢了个粉碎,那家伙立刻失去知觉,瘫在了一边儿。
片山将他拖入浴室,为使他不至停止呼吸,便将绳套松劲了一些,然后,抓过他搭在椅子上的衣服翻来复去搜查起来。根据从内衣口袋中翻出的船员证上所记的,此人的国籍是泰国,名叫蓬&iddot;沙姆拉克。片山将这家伙带着的三千美元现钞收好,又从他的上衣左胸袋里掏出一支除去枪套的枪,这是一支短枪身的轮式手枪。
片山撕下床单,塞进这家伙口中,接着又用他随身携带的打火机,凑近他的鼻孔来回灼烧着。顿时,这人鼻孔里传出一阵焦糊气。他发出一阵呻吟,总算又恢复了知觉。
&ldo;你叫什么名字?&rdo;片山将滚烫的打火机扔在瓷砖地上,用法语问道。
&ldo;你,你是谁?混,混蛋!哎,哎哟……&rdo;那家伙痛苦地呻吟着。
&ldo;我问你姓名,蓬是假名吧。&rdo;
&ldo;你怎么知道?&rdo;
&ldo;能说法语的泰国船员还不怎么多见,除非是昔日法国殖民地的越南人。&rdo;
&ldo;畜生……我叫格渊,越南西贡人,是因战败逃到泰国去的。你到底为什么这样恨我?&rdo;
&ldo;没什么……,只要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不至于再吃苦头。&rdo;
&ldo;畜生……&rdo;
&ldo;当帕罗玛号离开日本时,你在船上吗?&rdo;
&ldo;帕罗玛号,这是怎么一回事?&rdo;
&ldo;别装蒜……啊,我明白了,这好办,可以让你再也无法和女人亲热。&rdo;
片山取下挂在墙上的毛巾,卷在左手上,拽出格渊的生殖器,将右手握着的匕首搁在上面。
&ldo;住手……千万……饶了我吧……庞萨号的确就是帕罗玛号,我是在新加坡港上的船。&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