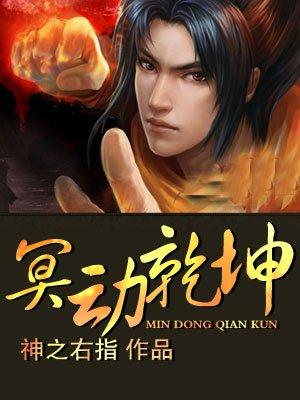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人鱼的诅咒 ... > 第6页(第1页)
第6页(第1页)
谢丹冲着年轻人展开一个略显生硬的笑容,然后飞快地朝着两边的门窗扫了一眼。我和聂行藏身的位置都较为隐蔽,因此一眼扫过之后,谢丹脸上流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她微微低下头,带着仿佛是犹豫不决似的神情开始快速地说起话来。坐在她对面的年轻人即使到了室内也没有解开那条黑白格子的大围巾,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她,不时地点点头,示意她继续往下说。在这个过程中谢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大的起伏,但是不知怎么就是让我微妙的觉得,她似乎越说越没有底气。“科学家有不少事情瞒着咱们呢。”我悄声对聂行说:“她跟这人是约好的。”要不然不会一大早就提醒我们各自解散,有事情了打电话联系我们。问题是安保这个行当,有像她这么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么?“也不知道她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光是安保就请了两拨人。”聂行嘀咕,“连行动队都被打发出来了,好大声势……”“我怎么觉得不像是有仇家的样子呢……”“这人要出来。”聂行打断了我的猜测,低声咒骂,“该死的围巾!”戴着围巾的青年果然站了起来,低着头穿过快餐店,沿着来路匆匆走了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朝着我这边的方向飞快地回了一下头。一闪而过的目光锋锐如刀。不等我看清楚藏在格子围巾下面的那张脸,他又飞快地转回身去快步离开了。但是萦绕心头似曾相识的感觉却越发鲜明了起来。我又想起他身上的那件大衣,那种严谨而又优雅的完美主义风格在近期之内我还真看见过两回。不过,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脸,仅凭着一点模糊的印象似乎还不能够得出什么结论。聂行低声问我:“咱用不用追?”我摇摇头,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回来。我们现在什么事情都不了解,实在不适合把摊子铺的太大。再说谢丹也已经结账离开了快餐店,这个时候分出一个人去做别的事并不妥当。聂行跑回来的时候又问我:“这些科学家都开始逛街了,是不是大会开完了?那咱们的任务呢,是不是也完事儿了?”“这恐怕不是咱们俩说了算的。”我挽住他的胳膊,冲着谢丹离开的方向抬了抬下巴,“她去海边了。”“你说这人也真有意思。”聂行嘀咕,“让人保护,又啥底子都不露。真是的。”我安慰地拍拍他的脑袋,“跟上吧。”谢女士顺着广场边缘的台阶走到了沙滩上。冬日的海滩略显萧条,海水在阴沉沉的天幕下呈现出浑浊的灰色,泡沫般的浪花卷上沙滩,又迅速退回去,然后再一次不知疲倦地涌上来。谢女士的大墨镜已经摘了下来,她眯着眼睛望着远处的海面,一脸沉思的表情。听到我们靠近的脚步声,她头也不回地说:“抱歉,我恐怕还得麻烦二位。”见我和聂行都没有出声,她回头看了看我们,略带歉意地说:“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是有个学术访问,是去另外一个地方。顺利的话,用不了一周的时间。你们看……”她嘴里说的是“你们”,但目光却只盯着聂行。我猜是因为聂行是她的上级领导替她安排的,而我则只是她私人雇用的。“您太客气了。”聂行忙说:“在您回京之前,我的任务就不算完。”谢丹的表情放松下来,流露出一个真心的微笑,“谢谢。”“可以问问是去哪里吗?”我问她,“什么时候动身?”“是一个研究所。”谢丹沉吟片刻,缓缓说道:“这个研究所建在一个岛上,距离岛城并不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明晚动身。”x先生我和聂行很快就知道了明晚动身的用意。转天一早,谢丹的两位助手就匆匆赶到了裕华街。两位男士的年龄都在三十上下,不怎么爱说话的样子。谢丹带着他们在书房里面对厚厚的资料一忙就是一整天。我一直怀疑谢女士的行程变动跟出现在快餐店里的那个男人有关,是一桩胁迫事件。但是看这架势,这似乎是一次很正式的学术访问。就连坐在车里的时候,这三位学者仍然对着笔记本心无旁骛地讨论着我们听不懂的学术问题。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透过干枯的树干的缝隙可以看到远处灰色的海。海面上笼罩着薄薄一层雾气,几乎模糊了海与天的界线。视线的尽头,一个琵琶形的小岛已经在灰色的雾气中模模糊糊的现出了轮廓。谢丹所说的这个岛名叫石头岛。确切的说它只是一个半岛,位置很偏,面积小到地图上都没有标注。从罗升发给我的资料来看,这片区域的全名叫做“石头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但实际上除了药品公司和规模不等的几家研究所之外,这里连家杂货店都没有。谢丹将要前往的就是其中一家名叫捷康的生物制品研究所。随着夜色降临,雾变得越来越浓。一团一团,像吸饱了水分的棉花似的聚拢在我们周围,即使开着车灯能见度也不超过百米。橘黄色的灯光透过雾气暖暖的照着空荡荡的街道。远处的海、甚至公路旁边那些空荡荡的厂房都被遮挡在了浓重的雾气后面,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样的天气总会让人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何况这里还很静。没有城市里的喧嚣,连海浪的起伏也似有似无。我甚至分得清车厢里每一个人的呼吸声。两位助手似乎有些恹恹欲睡,而谢丹女士的呼吸声反而急促了起来。我和聂行飞快地交换了一个视线,谢教授到底在紧张些什么?“大概就是这里了,”谢丹气息不稳地提醒聂行,“再往前一点儿。”再往前一点儿的地方已经有灯光透出来。不是路灯,而是机关大院的传达室里透出的那种灯光,在夜色里显得安静而又疏离,微带冷意。借着这一点模糊的亮光,可以让人影影绰绰地看到大门旁边那块写着“捷□□物研究所”的牌子和挡在门前红白相间的一道横栏。不等聂行停好车,我就推开车门跳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弥漫在我们周围的遮天蔽日的大雾,也许是因为岛上诡异的安静,我心里隐隐的生出了几分不那么美妙的预感。谢女士的一位助手跑过去敲了敲传达室的玻璃,将一个类似于介绍信之类的东西递了进去,不多时拦在大门上的横栏慢慢升了起来。传达室的门打开又阖上,一个矮胖的身影踢踏踢踏地走了出来。“车停左边。”一个男人粗声大气地吆喝,“我带你们进去。”大门左边就是停车场,隔着雾气模模糊糊地看到停着几辆车。我和聂行一左一右地护在谢丹女士的身边,那两位助手先生反而被甩到了身后。“这边,这边,”走在前面的门卫被雾气模糊了轮廓,只有声音听起来依然中气十足,“已经给楼里打了电话,他们派人出来接你们了。”“麻烦你了,师傅。”谢丹走得急,声音微喘。“没事,没事。”门卫走在外面前面米的地方,我始终看不清楚他的脸,这让我心里觉得不踏实。手腕上一直不停跳动的数字表盘在走进这个大院之后也十分突兀地变成了两条微微起伏的直线,看样子,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联系上罗升和他的外援小队了。我抬头看了看走在另外一侧的聂行,他似乎也有所察觉,娃娃脸上难得的流露出凝重的神色。一幢灯火通明的大厦慢慢浮现在雾气中。两个颀长的身影顺着宽大的台阶迎过来。走在最前面的男人穿着浅色的衬衫,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也许是出来的匆忙,大衣的扣子没有系好,长长的衣摆随着他的步伐在身后飘来晃去,像两只黑色的翅膀。“谢教授,这边请。”男人的声音有种沁人的冷意,听在耳中仿佛碎冰块轻轻撞击着玻璃杯,“会议已经开始了。”我脑海中顿时警铃大作。这是我曾经听到过的声音,就在不久之前,这个声音曾用一种嘲谑的语气称呼那位被胁迫的少年为:x少爷。“x先生,”谢丹矜持地颌首示意,“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x少爷、x先生,这个符号应该是指同一个人。但若真是同一个人,此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男人又怎会称呼别人为x少爷?“谢教授,会议只给您留了两个席位,您看……”x先生摊开手,颇有些为难地停住了话头。雾气挡住了他的脸,看他的动作,似乎正来回打量着我们一行人。谢丹也迟疑了起来,“既然这样,我带小李进去。其他人等在会议室门外可以吗?”“当然没有问题。”x先生一口答应。谢丹冲着我和聂行略带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只能麻烦你们在门外等我了。”我和聂行同时点头。前几天也是这样,谢女士开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等在门外。大会工作人员曾解释说他们讨论的内容牵扯到很多专利技术,不方便让外人旁听。我想x先生的两个席位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是这个诡异的地方、这个身份成谜的男人,都让我心头的不安成倍滋长。“时间紧急,您和李先生先跟我进去,”x先生看了看她身后的人,又说,“我让秘书安排您的随行人员先去休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