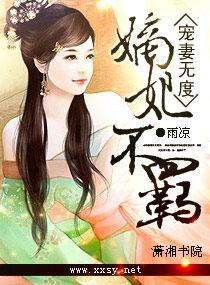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的厚脸皮女友顾冉最新章节免费阅读 > 第251章(第1页)
第251章(第1页)
即便睡着,潜意识里她还是觉得疼‐‐那个打针的人不仅扎针,还绝对给她做了皮试!皮试最痛!简直是童年阴影!小时候她胆子大,看到蛇都不怕,唯独见皮试一次嚎一次!
昏睡的她想说话,想抗议,想嚷嚷着发烧没关系,来包退烧药就好,皮试走开……
然而,思绪清醒,四肢却浑身无力,身体机能像是仍在脆弱修复中,根本无法转醒……于是她只能挨着痛,被迫在这断断续续的睡眠中,翻来倒去,浮浮沉沉。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反正手腕上的针扎了几次,痛得她在梦里哆嗦了好久……不过要说的是,疼痛归疼痛,那针里应该加了些营养物质,她这疲惫脆弱的躯壳,仿佛濒临脱水的植物,终因外界的滋养,渐渐充沛起来。
终于,在某个安静的傍晚,她醒了过来。
……
大雪消停以后,城市并未放晴,冬雨接替大雪姗姗来到,昏暗的天如暗色的画卷,雨滴敲在窗台的玻璃上,蜿蜒拉出一道道雨痕,天地间一派淅淅沥沥的迷蒙。
顾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睁开的眼。
映入眼帘的是个陌生之地,如果要用词语来形容,大概只有几个关键词,&ldo;整洁、干净、冷色调&rdo;,简直像男老师的单身宿舍。
浅灰色床单与地毯,前方摆满书籍文件的工作桌椅,浅灰的立柜,还有窗户旁边灰蓝色的窗帘……以及,三十公分以外,穿着灰蓝色衬衣的男人背影。
这男人跟她的距离十分之近,说穿了就是坐在床头,眼下正拿着个文件夹阅览,似乎是在加班。
大概是察觉出她的动静,男人扭头一看她,乌眸迸出光亮,&ldo;醒了。&rdo;
声音如释重负,像是守候多时,终于等到她安然无恙悠悠转醒。
旋即他放下自己手中的文件夹,俯在床前,凑得更近地问她,&ldo;感觉怎么样?&rdo;
床上的人将醒,意识还有些迷糊,没答他的话,只迷蒙地睁着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好半天才问:&ldo;这是哪啊?&rdo;
谢豫道:&ldo;我家。&rdo;
床上的人瞪大眼,要不是这副身体将醒中绵软无力,她铁定得弹起来。
那边谢豫见她吃惊的模样,补充道:&ldo;我巴黎的住所,跟法方合作,需要长期处理这边的事务,我就在这买了套公寓……这里安静,适合休息,从医院出来后,我就把你带到了这,你发烧,已经在这睡了三天。&rdo;
&ldo;三天!&rdo;顾冉蒙圈的大脑终于想起了最要紧的事,这会是真要弹起来,&ldo;我爸这么样了!手术后来怎么样了?我要去医院……&rdo;
她光着脚就往床下蹦,谢豫伸手拦住她,将她按回了床上,&ldo;手术很成功,你爸一切都好,现在你妈陪在医院,迈克尔医生也在全天候观察中,你不用担心,在我这好好休息。&rdo;
见顾冉坐在床沿,即便被他拦着,还晃荡着脚丫子低头想找鞋,谢豫无奈道:&ldo;真想去,你也得吃些东西再去,我去叫人给你做点粥,你等会。&rdo;
……
等粥的时间,顾冉又躺回床上。醒来后她没了睡意,就睁着大眼睛,去看着窗外的雨。
而谢豫,重新坐回到一旁。
顾冉以为他会继续去加班,可他没有,他就一直坐在她身后。
大概是房间太过安静,顾冉看了会外面的雨,忍不住从被子里扭头,就看到谢豫靠在她背后的床头,就那般凝视着她。
这个姿势,在她潜意识的感官中,也许高烧昏睡中的她,被他曾无数次这般看过,她没由来有些局促,扯了扯身上的被子,故作漫不经心,&ldo;你干嘛老看着我,去加班啊。&rdo;
谢豫仍是看着她,半晌他说:&ldo;你这两天发烧,可折腾死人了。&rdo;
顾冉一愣,注意力停在&ldo;这两天&rdo;一词上。
而也是这一瞬间,那些潜意识里的诸多感受,在这将醒不久后的傍晚,因为这一个词,如潮水般统统回放。
其实潜意识里,她对这两天昏睡的过程,隐约有些残留的印象。
从昏睡到高烧,再到醒来,总有一个人陪在她身边,给她量体温,给她喂药,请医生来看病……明明那样寡言高冷的性子,却在跟医生问她状况时候,细细问了大半小时。
她曾抗拒过打针,一旦打针,睡梦中都要疼得哼唧,而每到这时,总有个人在她耳边,握着她手腕,安抚般道:&ldo;不痛不痛,很快就好……&rdo;
白天那个人守着她,夜里那个人还守着她,她潜意识里许多个浑浑噩噩的瞬间,他好像一直就呆在这个房间,时不时给她掖腋被角,换额上的发烧贴,给她擦脸擦手……怕她口干,他还用棉签沾水给她湿润嘴唇,偶尔她哼唧着渴,他便小心将她头托起来,喂她水喝。
不仅如此,他好像还对旁人立了许多规矩。
譬如,他的下属来这探望,他不允许人抽烟,不许脚步声过大,手机必须调静音,便是说话,一个个都是压着嗓子的。
所以,这一场昏眠,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也许是不甚好的经历,可她因为有这个人的无微不至,舒坦而安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