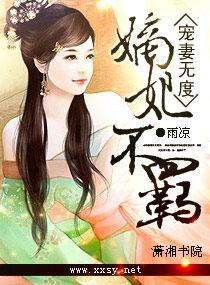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替身梗渣攻 > 第115章(第1页)
第115章(第1页)
师隐都没有给他泡过一壶茶。
也未曾同他手谈过。
韩宗言转着小指上的指环,回话道:“有。”
“他问我,为什么邀他入京。”
阿鸾问:“没了?”
韩宗言就说:“没了。”
他实在不知道自己一大早被撬起来跑一趟大兴寺,又回来坐在这里看皇帝的脸色是为的什么。
大年初一就过的这样。
韩宗言暗暗叹气,这一年怕是都要不得安生了。
阿鸾没再为难韩宗言,挥挥手让他回去。
韩宗言便赶忙告了退走了。
阿鸾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亏了什么似的。
师隐分明是他困在那里的。
可他却不是第一个喝到他泡的茶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与他下棋的。
阿鸾思来想去,到底没忍住,在夜里又悄悄去了精舍。
见到师隐,让他给自己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甚至连下棋时的落子先后都是没变的。
阿鸾也弄不明白自己的心思。
这太过明显了。
他也并非是冲动的人。
可就是忍不住。
忍不住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
初六的时候,阿鸾截住了师隐寄回去津州的包裹。
两封信,还有三本师隐手写的经书。
阿鸾拿着信,晃了晃,想看,又觉得不好。
便压下了。
到上元节那日,阿鸾没去精舍,只让人悄悄送了一盏花灯去精舍,他落了一个“鸾”字在花灯的灯芯里面。
这样一来,师隐就会知道是他。
而他也终于将师隐写的那两封信发了出去。
至于三本经书,则被阿鸾留了下来。
阿鸾并不看佛经,只是放在手边,偶尔瞥上一眼,就觉得安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