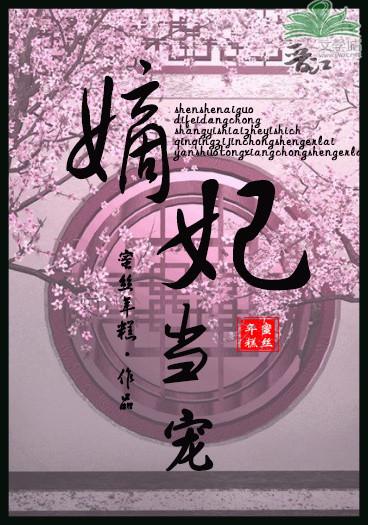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穿书后我每晚与反派互穿 作者想吃桃子 > 第10章(第2页)
第10章(第2页)
但她也不能一直不睡觉,算了,能拖一时是一时吧。
下定决心不睡觉的阮棠梨在书房内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却还是犯困。
两条大腿和胳膊上掐了好多个红印子,差点儿没头悬梁锥刺股了。
然而在黎明时分,阮棠梨还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阮棠梨出现在自己那个弥漫着臭味的小破屋。
一晚上没睡,她整个人累极了,眼圈乌黑,走起路来也头重脚轻,但是她的心情却很亢奋忐忑。
天色还早,阮棠梨尝试睡个回笼觉,却怎么也睡不着,只能极不情愿地穿衣起床。
整个上午阮棠梨如惊弓之鸟一般,精神极其紧绷,仿佛下一秒她就会被拉到刑房,被迫尝试所有刑具。
但是一上午过去,沈惊寒没找她,祁才也没找她,一切都风平浪静。
晌午时分,烈日炎炎,按照府里规定,奴才们可以回屋休息半个时辰再进行下午的工作。
也就这段时间,整个瑞王府显得格外安静和懒怠,风吹过树梢发出的沙沙声都成了催人入眠的音符。
然而书房内的气氛却与外面截然不同。
“撤兵了是什么意思?”
大概是刚睡醒的原因,沈惊寒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慵懒和沙哑,却依旧无法让人忽视其中的压迫感。
尤其是祁才这种跟了很多年的,只需一句话,他就知道现在王爷的心情极差。
“王爷,昨儿晚上奴才来书房向王爷报告部署的进度,王爷却忽然要奴才撤兵,奴才当时也大为不解。”祁才现在简直如履薄冰,万分小心地解释道。
沈惊寒将手里的茶杯往桌上一扔,茶水立刻前赴后继地涌出,染湿了桌上画了一半的画作。
“何时?”声音陡然降至冰点。
祁才一个冷颤,跪了下来,“大概亥时一刻左右,奴才得到情报,今日巳时三刻池怀述定会经过半马坡,特意前来禀告王爷,还把埋伏图给王爷过目了。”
越听下去,沈惊寒的脸色就越难看,祁才也越发底气不足。
“后来,王爷直接吩咐奴才要撤兵,还说得到了最新消息,池怀述不会经过半马坡……”
昨晚在书房发生的事仿若做梦一般,祁才现下复述出来,才惊觉昨日王爷的不同寻常。
他根本不敢抬头看坐在书桌后的人。
不过沈惊寒却没有如祁才所想的大发雷霆,他在回忆昨天晚上的事。
祁才说昨日来书房将最新消息禀告于他,到这里他确实有印象,但之后发生的事他却是一概不知的。
他只记得当时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困意笼罩,不过闭眼稍眯了片刻,再睁眼时就身处于那个上了锁的破旧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