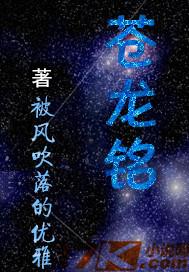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春尽江南端午和家玉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ldo;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代价还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当然,gdp还不错。据说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是吗?&rdo;
教授笑了笑,插话道:
&ldo;不是马上,而是已经。有时候,我们很世故,有时候似乎又幼稚得可笑。一头狮子,如果说自己长得有多肥,炫耀炫耀,那倒也不妨事的;如果是羊或猪一类的动物,整天吹嘘自己长得有多胖,前景反而有点不太妙。&rdo;
随后他又补充说,&ldo;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rdo;
研究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的思路似乎也被正在朗诵的诗歌片断打乱了。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我这活腻了的身体
还在冒泡泡,一只比
一只大,一次比一次圆
研究员把目光转向端午,问道:&ldo;诗人有何高见?你怎么看?&rdo;
&ldo;我是个乡下人。没什么可说的。&rdo;端午笑道,&ldo;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或者陈词滥调……&rdo;
&ldo;我同意。&rdo;研究员道,&ldo;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rdo;
端午觉得研究员多少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正想声辩几句,就看见吉士已经哈欠连天地站了起来,从椅背上取下夹克。
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
端午没有与他们一起去夜总会。
吉士暗示他,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和昨晚大不一样。女孩们都穿着红卫兵的服装。他许诺说,在灵魂出窍的疯狂中,还有浓郁的怀旧情调。不过,吉士见端午主意已定,也没有怎么去勉强他。倒是教授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睛,说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
&ldo;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乎?&rdo;
他们就在酒吧门外的濛濛细雨中分了手。
6
上午九点开始的开幕式很简短,不到十点就结束了。据说是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接下来,照例是代表们与当地领导合影留念。端午随着人群来到了宾馆门前,差不多已经到了他与家玉约定的聊天时间。
天虽然已经晴了,可空中依然飘洒着细碎的雨丝。端午利用照相前互相谦让位序的间歇,悄悄地离开了那里,打算溜回自己的房间。他穿过大堂,走到楼梯口,一位长发披肩的旅德诗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人微笑着给了他一个西方式的拥抱,然后递给他一份不知什么人起草的共同宣言,让他签字。端午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林。那年在斯德哥尔摩,他们在森林边的一个餐馆里,品尝北欧风味的猪蹄时,两人匆匆见过一面。端午有些厌恶他的做派与为人。
&ldo;老高问你好。&rdo;他笑着对端午道。
&ldo;谁是老高?&rdo;
&ldo;连老高都不记得了吗?七八年前,我们在斯德哥尔摩……&rdo;
端午很不耐烦地从他手里接过那份宣言,也没顾上细看,就心烦意乱地还给了他:&ldo;对不起,我不能签。&rdo;
旅德诗人并不生气。他优雅地抱着双臂,笑起来的时候,甚至还带着一点孩子气:&ldo;为什么?我能将它理解为胆怯和软弱吗?&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