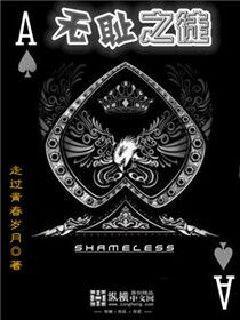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一旦she进去就无法流出来魏承泽 > 阿卿二更(第2页)
阿卿二更(第2页)
花瑾将冻僵的手蜷缩进宽大的卫衣中,低下头把自己的脸埋进衣领,只露出一双恹恹的眼睛,眼皮在不断的打颤,即将要掩合住的瞬间,又急忙睁开。
被扇紫的颧骨,也不由泛起了微红,不少出租车路过她都纷纷鸣笛,她也毫无反应。
越来越困了,她好想睡觉,就算躺在街上睡死过去也愿意,只要现在能马上入睡,她做什么都愿意。
好像是发烧了。
耳边传来的声音让她蓦地睁开眼,眼前进入的深棕色大衣,看起来好像十分的暖和。
她睁不开眼,但竭尽全力的想看清面前来人,努力的抬起头来。
而她模糊中只能看到路边停着一辆白色轿车,就如同面前这身大衣一样成熟。
先把她抱上车。
不是吧,你
不能不管。
啧!
丁子濯无奈只能接过他手里面的伞,看着他将人抱起,匆匆把伞举高在他头顶挡住雨水。
伴随着雨滴嚣张的拍打声,他们弯腰进了温暖的车中。
宽大的怀抱,令人熟悉又幸福的香味,她没有犹豫的入睡,手心里还紧攥着男人大衣上的纽扣。
香甜热可可的味道窜入鼻腔。
她眼皮困的挣扎中睡了很久,有人温柔的将她叫醒,哄孩子一样轻声。
先把药吃了再睡。
花瑾,花瑾。
听话,把退烧药吃了。
她微张着干燥唇瓣,呼吸加重,睁开千斤顶一样的眼皮,看到那双眼睛中的自己。
阿卿。
是我。
得到回应,她热泪盈眶,吭哧吭哧哭出声,丝毫不觉手中还抓着他的衣服:阿卿,阿卿,我没做梦,阿卿。
他半垂着眼睫,睫毛在焦黄色灯光下显得挺翘温柔。
没有做梦,把药吃了再睡。
花瑾蔫头耷耳,抓着他的手臂想要起身,试了很多次都重重跌回沙发上,塌陷进柔软的布料里。
有力的手臂扶住她肩膀一把搂起,宽大掌心中放着几粒颜色不一的药物,送到她的嘴边。
背后的丁子濯一阵冷嘲热讽:还在这博取你同情呢教授,装什么装,要是把她扔在那,看着她烧死才叫过瘾。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瞧瞧她脸上的伤,那恐怕是撒谎被打出来的伤口啊,教授,你还准备被她蛊惑到什么时候?
她被水呛到咳嗽,男人慌张拍打着瘦弱的脊背,丁子濯压着眼皮,满腔不悦。
别走,求你了别走,陪我一会儿也好,求你。
我不走。习卿寥抓住她伸在半空中的手,冰凉的温度刺激着他灼热掌心,轻声叹气:睡吧。
碎碎念分割线
一个小小小秘密谁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