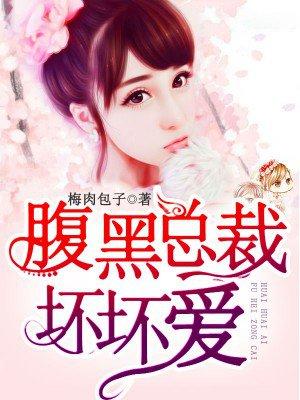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小肥啾饲主总想吃了我 > 第26页(第1页)
第26页(第1页)
她们说话的声音最终在冬早的耳畔渐渐消失,等冬早再醒过来时,一早上的时光已经没了,他也好不容易捡了一点精神回来。冬早站起来抖了抖自己的羽毛,先是有些茫然的站在桌上停了一会儿,等弄清楚自己在哪儿以后,冬早扭头啄了两口小米粒又喝了两口水,而后他才飞起来。屋外出乎寻常的热闹。陈起明带着几个副将来看萧绥,此时正在书房里头说话。冬早一上午没有看见萧绥,此时就像见见他,他照常飞到书房门口,想要侍卫给他开门,好让他进去。平常时候门口只有婢女守着,她们一见着冬早是铁定马上帮他开门的。但侍卫不同,他们目不斜视,任凭冬早在书房门口盘旋来回,亦或是殷切的盯着他们瞧,全只当没看见一般。若是冬早靠窗户太近,还会有人将他拦住,亦或是不耐烦的赶的远一点。冬早给这么一弄,十分委屈,只能扭头眼巴巴的站在小树杈上等待。外面冷风阵阵,吹到人身上凉的瑟缩。冬早停在树上却不觉得多么凉,这两天他一直觉得浑身热乎乎的,不算难受。书房里。陈起明怒气冲冲,“如今看来,这些都是皇帝的计谋了,查了五六天不说进展,连头绪也没有一点儿,还不许我们查收,另外一边,又扳倒我们这边两个人。”皇帝那边现在传来的种种行动,都是摆明了要架空萧绥手上的权力。此举惹来萧绥手下不少大将的不满,陈起明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一个。“西北兵士现在如何?”萧绥脸上却是淡淡,开口先问起的还是先前传来物资匮乏的西北兵士。西北那边数国虎视眈眈,是一刻都不容迟缓的。陈起明一愣,后照实回答,“西北情势目前还稳,属下这里还有一封今天早上刚到的信报,”他说着将信纸递给萧绥。萧绥一边过目,陈起明一边继续说,“只不过现在的情势不过暂时,西北各国狼子野心,断然不会是安分的角色,如果守的不紧,眨眼睛就能出事。”萧绥浏览过一遍信纸上的内容,沉吟道,“如果明日早朝还有人提起西北驻兵之事,只管顺从他们的意思,要撤军就撤军,往后退三十里,做收兵之势便是。”“王爷,”陈起明瞪眼,“这怎么成?”萧绥将那信纸揉成一团,随手抛进火堆里燃烧干净,冷声道,“如他所愿。”他说话果断干脆,下面的将士们也便都应承下去,对萧绥的话深信不疑。刺客一事,萧绥也命人调查过,种种线索追查下去,均指向深宫之中。其中有两种,要么是爱子心切的太后,要么是皇帝自己动了心思。但是萧绥清楚知道太后和皇帝的秉性,他们母子两人都缺乏为政者的果敢与谋略,如此密不透风无法追查出结果的事情,倒不像是他们能够做出来的。只不过,无论刺客是谁派来的,为的都是背后的皇帝。萧绥不是软柿子,他不打算任人拿捏,他们若是要耍手腕,他自然也会。冬早在树上等了不知多久,差点儿又睡着的时候,书房的门终于开了。他就怕门一会儿又关了,连忙一鼓作气的猛冲进去,气喘吁吁的停在萧绥的书桌上。陈起明还没走,乍一见冬早还吓了一跳,“哎,这是……”他仔细的看向冬早,有一会儿才想起来,“这不是那次在山上的鸟吗?”陈起明早就将冬早抛到脑后,也没想到萧绥还能真养着他。“嗯。”萧绥抬手,将冬早抱在手心,戳了戳冬早的脸颊,“粉毛都不见了。”冬早仰面仍由他弄,心里美滋滋。萧绥手一松,冬早就飞起来,贴着萧绥的脸颊来回蹭了两下后,停在萧绥的肩膀上紧紧的依偎着他。陈起明跟在萧绥身边十几年,从没有见他和什么人或物如此亲密过,更别说他对冬早亲昵的动作连半点不喜的地方都没有表现出来。他压下心底的吃惊,一步三回头的告退下去。等屋里的人一走,冬早立刻忍不住开口说话了,“我最近好喜欢睡觉啊,”他对此也其实很烦恼,“是因为你在家的缘故吗?”萧绥不解,“这和我在家有什么关系?”“我好像一看见你就想睡觉。”冬早说。比如现在,他张开嘴,发出困倦的哈欠声,“我好困好困。”萧绥笑起来,正想说话,忽然觉得颈间一阵出乎寻常的热烫。前一刻还不停说话的冬早咕嘟嘟的从他的肩膀上滚了下来,落在萧绥托住他的手心上,像个小火球一样滚烫。“刚才他们都不让我进来……”冬早小心抱怨,语气已经因为睡意而含糊起来。“嗯,他们做错了,下次让他们改。”萧绥托着冬早,略微皱起眉头来揉了揉冬早的脑门,“你难受吗?”怎么会忽然浑身热成这副模样。冬早已经快困得说不出话来,“嗯……嗯,不,不难受啊……”他说着便沉默下去,白色的羽毛间骤然闪起一团朦胧的光晕,一瞬间迸射出来,让萧绥愣在了原地。这一霎那的光芒转瞬即逝,使得人不得不怀疑它是否存在过。纵使是萧绥,他也惊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只不过这会儿过后,冬早身上的热度慢慢就降了下来,也没有再表现出任何与平常不同的地方。而冬早,他做了一个悠远绵长的梦。他被花瓣包裹着,浑身清亮通透,周围天地之间一片水雾迷茫。冬早有些迷糊,他现在在哪里啊?他转头四处看,视线之中却都是一片粉色。他好像坐在一朵花里面,仰头能看到的也不像是天空,反而像是一大团流动的水,仿佛一戳就会破。冬早正觉得奇怪,忽然听见一串小小的人声,“快些送过去,仙君那边掐着时间的。”冬早费劲儿的仰头望外看,几个小仙童模样的人从自己身边快步走过,衣摆不小心牵扯到花瓣,让整朵花都晃晃悠悠起来。冬早坐在里头被弄得头昏脑胀,差点儿昏过去。就在此时,一双手忽然温柔的托住了花苞,将冬早的折磨结束了,他仰头看,萧绥的指尖点在了花苞上头。冬早站在镜子前面盯了自己的脸小半天,又仔细规整了自己的羽毛,终于觉得丑的并不过分了,他才哼哧一声从镜前的桌面上跳到一旁的小几处,扑棱两下翅膀,房里此时就他一个,任凭他上蹿下跳了好一会儿,也没听见外面一点儿响动。冬早有些烦恼。他最后停在窗口发愣,因为年节将近的缘故,胖瘦婢女这段时间以来都忙,且又给萧绥下令说不能看话本了,她们最近凑在一起也就是做做针线活,说一说天南海北的事情。完全失去了学习源泉的冬早,有些不太知道怎么向萧绥求爱才是正确的了。加之,冬早其实有点怕。他也察觉到了自己这些天的异常,浑身觉得忽冷忽热的不说,有时候几乎是一瞬间就倒头睡,和萧绥在一起的时候还好,他总能一手将冬早捞起来,然而有些时候没那么凑巧,他自己咕嘟咕嘟就从桌子上滚下去,摔得腰酸背痛。可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古怪呢,冬早自己傻乎乎的也想不出来原因。胖瘦婢女吃了午饭回来偏房烤火做针线,推门时见着了冬早寂寥的背影,胖婢女抿唇笑,“胖胖成天倒像是个有心事的人一般,深沉的很啊。”冬早闻言回过头来不太欢喜的盯了胖婢女一会儿。他想,我本来就很深沉,不要看不起鸟。瘦婢女端着针线篮子低头坐在榻上,闻言说,“谁说胖胖不能有心事啦,这人啊鸟啊的,保不准都有自己的烦心事,我们又不清楚。”冬早听了这话颇为认同,觉得瘦婢女有想法,唧唧叫了两声以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