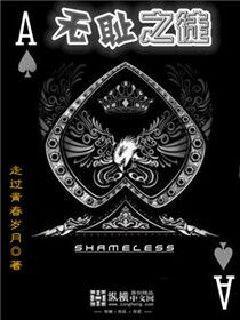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老九门启月续写虐新月 > 第50页(第1页)
第50页(第1页)
张启山只觉得一阵尖锐的疼痛自后脑流窜到太阳穴,像一把利刃生生将他的脑袋锯成了两半。一半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真相,另一半则愤怒的叫嚣,几乎如同热油烹灼烈火。“在你们心里,张日山就是那种人?!”皮鞭声还在响,带着倒刺的皮鞭抽打上少年单薄的后背,一鞭下去、就刮下一块血肉。少年起初还能闷吟出声,却很快连气音也难辨了。他仿佛跌入深沉迷梦中的旅人,印在身后的每一鞭子都在强迫他从幻境中苏醒。一盆沁心凉的盐水被泼到了伤口上。“啊!——”少年终究是耐不住,低哑惨呼。酒井一把揪住了张日山的头发,戴着白手套的指尖摩挲过少年后颈上的腺体:“乾元,”他的中文带着怪异的腔调,“你的乾元,在哪?”他已经发现了张日山坤腺上被啃噬过的痕迹,这个坤泽必定已经被乾元标记,而乾元可是比坤泽更加金贵的存在。没准……就是一方的高官镇守。交上去,前途大大的有!疼,日山只觉得浑身无一处不在疼,尖锐的疼痛变成了沙缓的磨砺,沿着他的神经节节攀咬。可他不能说,他杀了张泽洋就是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又怎能从他口中倾吐出去?狠狠一拳塞上了少年的胃。他哇地一口将胆汁都要呕出来了,双臂的桎梏却让他连身体向前倾斜也不能,徒劳的弹回原地,最后一点气力也在击打中耗尽。但酒井有的是折磨人的办法,他的手指抠入日山被鞭子割出来的伤口中,手指卡入最深的破疮处,用力翻搅、抠挖。“呜——啊……!”少年垂首忍耐着,却终究压不住喑哑的哀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酒井用他没有染血的白手套拍拍少年的面颊,“我们的医务室前段时间丢了一瓶磺胺、碎了一支抑制剂。我现在知道,那支抑制剂并不是意外碎裂的了。可是……你的乾元,一定不在很远的地方。”他笑起来,咧出一嘴黄牙。“你在努力的活下去,等着你的乾元来救你,或者、带你出去。”日山克制自己的呼吸,不要有丝毫的紊乱。“告诉我,他在哪?”“家主,我们必须撤退。”精锐的声音冷肃的不容辩驳。这就是老宅与本家的区别,老宅的张家人,永远守护正统,哪怕任务与情感相悖。当然,或许也有私心,毕竟十七条命填一条命,不划算。张启山的胸膛剧烈起伏着。“营座。”“营座!”张家军们也不能忍了,他们忍耐了太久,再待下去,只要张日山一个扛不住松了口,他们全部都得死。而且在他们心中,一个为了玉佩就可以杀死同伴的人,也肯定不会为营座豁出生命,更不配……他们为他搭上性命。张启山闭了下眼睛。“……松绑。”他其实早就瞧好了一处地方,还是上次日本人的车拉着他们外出劳作时,他与日山一出的一处五爪型墓穴,墓穴地处背阴低洼处,白虎凶煞,大概墓主得罪了什么人才被埋葬于此。年久墓松已经露出砖石,如果他们能乘夜翻出铁栏的封锁逃入墓穴中,捱过日本人的搜查,就可以从那里逃出升天。日本人的探照灯与岗哨并非万无一失,上次他与日山已经利用偷抑制剂的功夫印证了。逃跑的计划本来定在十天后,他从来没想过要丢下少年离开,可他确实不能拿十七个人换一条命,更何况,还换不来。张启山知道日山绝不会为了玉佩谋杀,但却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罔顾最终十七个兄弟。他最终将自己的心意抛掷脑后——他先是营长、家主,才是张启山。日本人将张日山从架子上解了下来,二十长鞭之后,少年的后背上交错的全是血痕。血痕从颈项后起,一直蔓延到臀根,拉破本就破败的衣物,让少年几乎要在冬日的夜风中衣不蔽体。酒井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将绳子拴在少年的脖子上,像牵着条狗一样的牵着他,拉拽着少年向前。腿上的伤势、后背撕裂的伤口,让日山的每一步都似迈在刀尖上,他从咽喉中呼出残破的气流。几个日本兵在后面摸他的屁股与背脊,被标记过的坤泽与其他任何中庸、乾元交合都只会自动封闭内腔,浑身剧痛。所以拿一个坤穴紧得会把自己下体绞断的坤泽发泄性欲,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当然,不是说他们不想,而是时机未到,用这个坤泽钓出个乾元显然是更好的买卖。所以,要先激怒这个乾元。但酒井不介意给他的士兵们一点福利,早晚会被狼瓜分的肉,让他们先舔一舔也没差。日山吃力地闪躲,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身体被他人触碰,但他的双手被捆在身后,嘴里被塞了一团肮脏的布,连自杀的余地都没有。腿上的伤势终于让他摔倒在泥地里,脖子上的绳索没有解开,那日本军官甚至拽着他向前拖行。日山其实已经不在乎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了,他甚至希望可以引起大一点的骚乱,这样……家主或许就可以乘乱逃出去。他被拉拽着在一间间营房面前巡游,酒井虽不认为他的乾元在这群劳工中,但是凡事都有个万一。日山被拽过张启山所在的营房时,不自觉朝那里偷偷多瞥了两眼。旋即他面朝下摔跌下去,不敢让自己的“偷窥”留下半点痕迹。虽然是在劳工营,但这里已经是他们相处过的最长的一段时间了,比过去五年的交集都要长。难怪家主要骂他的感情“可笑”了,连他也要觉得自己爱的可笑。张曰山啊张曰山,不属于你的,占了位置也没有用。他闪躲着日本兵的手,他不怕死,可他不愿意,临到死都不愿意,自己被他人羞辱的惨状落入少爷眼里。他希望,大少爷能记得他。如果记得,多少也希望是好看一点的样子。张启山带着十七个人逃走了,他们跳入了沟渠,越过岗哨的封锁线,躲过日本人的探照灯。天际隐隐有些擦亮的时候,张启山站在沟渠的尽头,他回头望向日山被吊起来的地方。巡游无果后,少年又被捆回原地。十二月的北方风中已经带了雪,他知道日山在等,等他们都逃出去,就会找个机会咬舌自尽,或者用缩骨功脱开绳索撞上刺刀的尖端。张启山从来没有那么怕过。他不怕死,可是他怕的是悬在日山颈项上的刀。三牛用力一推他的后腰,于是张启山的感情被湮灭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家主、营座的职责。“走!”他带头撑身而上,在满是泥泞的草稞子里匍匐,将多年的军事技巧发挥到极致。他很快接近了最后一道防护网,只要剪断那里的铁丝,就是一块空地。穿过空地躲入林子里,至少有八成的机会可以逃到那座白虎凶煞之地的墓穴,然后瞒过猎犬,逃出升天,把日山留在身后……他将最后那半句话的想法猛地咽下去,像活吞了一堆的钉。身体骤然前扑,肩膀撞上木桩,他蹭着木桩翻过身仰面躺在那铁网之下,摸出在劳动中顺来的钳子,绞断其中两根绕在一起的铁丝,在防护网上开出了一个堪堪容人通过的大洞。“快!”张家军的逃命速度史无前例的快,张启山忽觉有些讽刺,他们哭着喊着要来,这会又哭着喊着要回去。军人是个很奇怪的职业,在热血烧脑时候可以用胸膛挡住炮弹,兄弟意气一己之躯捍卫家国天下;冷静下来细细思考软刀子慢磨,却也各个惜命。但人性如此,他理解,所以他不怪。“一、二、三……”他拍着他们的后腰点着个数,想将他们一个个都带回去,“……十、十一、十二。”他的胳膊被三牛一把抓住:“营座,你先走!”张启山的喉咙滚动了下,他挥开三牛的手,揪住下一个着急钻狗洞的兵的后裤腰,稳住对方的身体将人往洞里送。哦,那个不是兵,一闪而过时他看清了脸,是阻拦他去救日山的那名精锐。三牛急得不行,被张启山狠狠瞪了一眼,他当然不会寻死,日山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他只是再想多陪他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