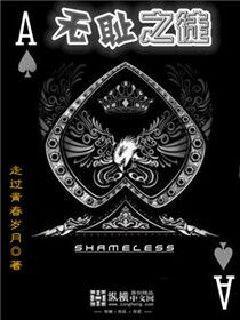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烟筒别墅之谜 > 第57章(第1页)
第57章(第1页)
“既然这样……”她突然止住本来要说的话,“怎么了?”
安东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树丛外面一个一板一眼立正站好的身影,那人就是那个赫索斯拉夫仆人——包瑞斯。
“稍等我一下,”安东尼对维吉尼亚说,“我去和我的‘狗’说句话。”
他走到包瑞斯身边。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主人。”包瑞斯向他鞠了一躬。
“很好,但你不要总是这样跟着我,看起来很奇怪。”
包瑞斯一言不发,拿出一张污损的纸片,显然是从一张信纸上扯下来的,递给安东尼。
“这是什么?”安东尼说。
上面只有用潦草的字迹写着的一个地址。
“他掉的,”包瑞斯说,“我拿过来给主人您。”
“谁掉的?”
“那个外国先生。”
“为什么拿给我?”
包瑞斯用谴责的眼光望着他。
“好吧,别管了,你走吧。”安东尼说,“我现在很忙。”
包瑞斯敬礼致意,利落地一个转身,大步走开了。安东尼将纸片塞进口袋,回到维吉尼亚那里。
“他要干什么?”她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叫他狗?”
“因为他的举动像只狗。”安东尼先回答了她的后一个问题。
“他上辈子肯定是只猎狗,他刚才给了我一张纸片,说是那位外国先生掉的。我猜他说的是列蒙。”
“大概是吧。”维吉尼亚勉强表示同意。
“他总是跟着我,”安东尼接着说,“就像一只狗。也不说话,只是用他那圆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我。我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的也可能是艾萨克斯坦。”维吉尼亚建议道,“艾萨克斯坦的样子看着也像个外国人,天知道他说的到底是谁。”
“艾萨克斯坦。”安东尼有点不耐烦地说,“他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有没有后悔卷到这件事里面来?”维吉尼亚突然问。
“后悔?当然没有。我很喜欢。我这辈子一直在寻找麻烦。也许这次的麻烦比我渴求的更加麻烦。”
“但你现在已经脱险了。”维吉尼亚说,安东尼不同寻常的严肃语气让她觉得有点奇怪。
“不算吧。”
两个人默默无语,漫步了几分钟。
“有一些人,”安东尼打破沉默,“从不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平常守规矩的驾驶员看到红灯会减速或者停车。可能我天生就是个色盲,看见红灯就禁不住往前冲。到最后,你也知道,便闯下大祸。那是必然的,也是活该。总的来说,那样对交通并不好。”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严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