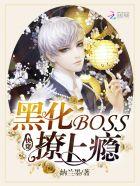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阿梨粤 歌曲晚风心里吹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阿梨仰头冲他笑,&ldo;都听你的。&rdo;
她说&ldo;都听你的&rdo;,软软柔柔声调,猫尾巴一样搔了下他心尖,薛延身子蓦的酥了一下,他恍然觉得,这份感觉比刚才同韦掌柜谈下了生意更让人觉得快慰。
攥着阿梨腕子的手更紧了点,薛延低低道,&ldo;待会去买鱼,我见那边有卖糖葫芦的,你爱不爱吃?&rdo;
阿梨乖顺说,&ldo;爱吃。&rdo;
薛延笑,&ldo;我给你买。&rdo;
野山楂又大又酸,红通通像是过年时候家门口挂着的红灯笼,上面裹着亮亮一层糖浆,浓稠的结成硬硬的壳儿,嵌着饱满的白芝麻,离了老远便就能闻着那股子酸甜味了。
薛延挑了根最大的,从小贩那里要了油纸抱住底下的木棍,轻轻放进阿梨手心。阿梨伸了舌小心翼翼舔一下,满足得眼儿都眯起,薛延揉揉她的发,拉着她手指往对街走。
只是刚走两步,却被一穿青色长袍男子拦住。那男子阿梨不认识,却晓得他身边跟着的人,是付六。
看着身前那只手,薛延脚步一顿,目光缓缓上移对上那人的脸,心中忽的似被拧一下。
他以往在京城横行霸道,早有人看他不顺眼,只未想到,他仇人在京城满大街,如今沦落到北地荒城,竟还能碰得到。
付六显然被薛延吓怕了,他咽不下那口气,但也不敢再招惹,见那男子一副要挑衅样子,忙慌慌拉着他袖子往后拽,道,&ldo;胡爷,走罢,兄弟们都等着喝酒呢,别再在大街上乱转悠了。再耽搁下去,菜就都凉了。&rdo;
付六一向嚣张跋扈,这样低三下气时候实在少有,阿梨咬着一半的糖山楂,目光不由瞟向他口中的那个&ldo;胡爷&rdo;。
年纪与薛延相仿,长得也不算差,神情里三分惊喜七分轻蔑,明明比薛延矮上三指有余,却有股居上临下的意味。胡安和嘴角忍不住挑起一丝笑,转瞬又被压下去,成一副淡然样子,冲着薛延拱了一礼,道,&ldo;薛四少,京城一别,许久不见啊。&rdo;
阿梨讶然偏头看向薛延,他们认识?
薛延唇线绷着,不咸不淡看回去,凉凉道,&ldo;胡公子,别来无恙。&rdo;
付六也惊了,视线在两人之间转来转去,问,&ldo;胡爷,你们这是……故交?&rdo;
胡安和笑着说,&ldo;哪里算得上是故交,薛四少哪里看得起我一小小光禄寺少卿之子,何况后来还被免了官。不过几面之缘而已,难为薛四少还记得。&rdo;他一拍脑门,恍然大悟样子,又道,&ldo;瞧我,光顾着叙旧,竟忘了礼数。&rdo;
胡安和微微弯了弯身,似笑非笑道,&ldo;不知薛老丞相近来可好啊?&rdo;
他这话一出,阿梨心中咯噔一声,忙拽住薛延胳膊。她本以为真是个来叙旧的老友,现终于分辨出,此人来者不善。
付六一脸茫然,问,&ldo;薛老丞相,什么丞相?&rdo;
胡安和说,&ldo;薛之寅,你不晓得?&rdo;
付六是真的迷迷糊糊,下意识道了句,&ldo;薛之寅不是因叛国罪斩首了,虽然这是个冤案,但最后不了了之也没别的动静,薛家不是就此垮了吗?&rdo;
胡安和拉着长音,一脸悲痛道,&ldo;啊,原来如此,我竟不曾知晓。&rdo;
这二人一唱一和如同说戏,而胡安和虽面上做着样子,眼神却毫不掩饰,内里似淬了毒钉。阿梨咬着唇,死死拉着薛延胳膊,生怕他冲动做出傻事。
薛延面上倒是风淡云轻,看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够了,才淡淡道,&ldo;承蒙胡公子惦念,薛某不胜感激。&rdo;
这样忍气吞声,不像他,胡安和一时间觉得诧异,半晌才冷笑一声,&ldo;人家说再坚硬的石头也是会磨平棱角的,我原本不信,现在看来此话是不假。当年仗势欺人如薛四少,如今也学会说客套话学会作假样子了。当年你在鹤云楼出言讥讽于我时的嚣张快意呢,尽数忘了?&rdo;
薛延还是那句轻飘飘的,&ldo;承蒙挂念。&rdo;
胡安和忽然觉得无趣得很。
他从袖中抽出一张红色信笺,上面金漆拓字,看着豪奢贵气,扬手扔进薛延怀中,道,&ldo;朝廷关怀,我父亲又能踏入仕途,做了陇县的县令。四月初三乔迁之喜,可请薛四少千万要赏个面子过来,我父亲见着你,定会高兴的。&rdo;
薛延两指捏着那信封,上下扇了扇,撩着眼皮看他,没言语。
他以往就是这样,目中无人样子,做什么都是懒懒散散,似是世间万物没什么能入了他的眼。胡安和恨他,不止因为两人曾经矛盾与羞辱,更是恨他这副桀骜姿态。原本薛延高高在上,他伏低做小便也就认了,可如今薛延沦落到比他还不如,仍是这样瞧不起人的样子,胡安和只觉心头无名火起,堵着嗓子眼一股地憋闷。
他咬着牙轻轻道,&ldo;薛延,咱们走着瞧。&rdo;而后也不等什么回应,连付六都没等,脚步匆匆便就离开了。付六忙着往上追,不忘回头看眼薛延神色,见他垂眸不语样子,心中暗自畅快。
总算有人替他出一口气。
阿梨虚虚扶着他胳膊,想说些什么,但也不敢出声打扰。日头渐热,糖葫芦上的浆都要化了,拉成黏黏的一条丝,薛延瞧见,抬手接过来把那半颗咬下去,问,&ldo;怎么不吃了?&rdo;